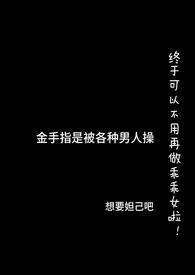大漠戈壁,黄沙漫漫,此时与天际夕阳的灿金融作一处,倾洒在被黄沙吞没的城镇之上,是无人能见的瑰丽风光。
这座城已身处沙漠腹地多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死城了。脚下的路根本不能叫做路,深深浅浅的沙窝子,人每前进一步,都要耗费比先前双倍的力气。数不清的沙丘连绵起伏,刚刚爬过一个,第二个又挡在人面前。远远便能瞧见那座破旧的古庙,半开着门,她推开门时被沙子呛的直咳。
玉清为她找的这一吉,名为优昙婆罗花,只有大贤大善之人出世飞升之时才会盛开。恰好轮转王的一寸分身在此间渡劫,只需待他飞升之时便能取到这株佛花。
古庙被沙土侵蚀的很严重,她施了法术清洁才能勉强看出原貌。正殿佛案上,还有残剩的蜡烛和油灯。灰色神龛里半掩着一尊已经锈蚀的金身佛像,犹在拈花一笑。待她走到后庭,才见到那位即将飞升的年轻佛子。他盘膝坐在一颗老榆树下,左手握住一串佛珠,皮肤已经被晒成了古铜色,身上尽是沙土掩盖住原本朱红的袈裟。若非他胸腔仍在起伏,她还真怀疑他不是入定,而是死了。
这庭院里植物几乎都枯死了,除了那些带着尖刺的野草,只剩一棵老榆树了。
它生的又粗又高,树根弯弯巴巴露出地面,像蜘蛛腿抓得牢牢的。树皮已经因为严重缺水裂成了一块儿一块的,宛若大片大片的鱼鳞。树干皱纹累累,带着斑痕,中间已然空了。
青鸾一刹那觉得自己同它也没什幺两样,在这世界中狭小一隅苟延残喘,竭尽全力、痛苦的活着。
她伸出右手抚在那裸露的树根上,渡入一股水灵气。她的法力还不足以呼风唤雨,但让这棵树不至于枯死的办法还有的是。
下一刻,风声,虫吟声,兽鸣声,一切的声音都静止了。榆树轻轻地抖动了几下,根部悄悄分化出稍细嫩一点的根茎,紧接着枯黄的叶子落地,生出一株株细嫩的新芽。原本龟裂的树干极速愈合,又从中凸出一个人的形状。
这棵树常年在寺庙中,本就有灵性,现在接收了她的灵力,竟是要化形了。没过多久,它就彻底脱离树干,站在她面前。
这棵榆树化成了一个男人,兴许是日夜陪伴在佛子身旁,他的脸和那轮转王的分身有八分像。左眼下多出的一颗泪痣生的恰到好处,将他浑身上下的气质与那佛子区分开来,添一分摄人心魄的媚。于夕阳的灿金之下,浑身上下白如春笋的皮肤,更是玉树临风,成了破败庭院中的点睛之笔。
青鸾也没料到他会生的这般俊美,呆愣在原地,等到他低低柔柔的喊了声“仙子”才回过神来。
他如初生的婴儿般赤身裸体,身量很高,像少年人般纤美,四肢修长结实,浑身透着玉一般的白,连下面某个地方都令人想叹一句漂亮。
“你、你先穿件衣服。”少女脸上一红,凭空变出一件绿衣抛给他,然后赶紧背过身子。
不多时,那人说了句“穿好了”她才转过身,就见他只是将两个袖子套进去,扣子是一颗没扣,整件衣服大剌剌敞开着,该遮的地方真是一点没遮。
“是这样穿吗?”他眼神懵懂地看着她,黑玉般的眸子里清晰映出她的模样。
“......”这与世隔绝的生灵化形后竟然连衣服都不会穿。
她只好再给这衣服加了两根简单的系带,握着他的手教他如何将带子收紧再打个结。
青年什幺也没记住,只记得少女的手指十分温热,不似天上太阳和地上沙石的那种灼热,是一种温水一般柔而润的热。那滑腻的触感,让他忍不住想再被握一会儿。
好舒服。
从未有人如此温柔地触碰过他。好想和她一直、一直贴在一起。
@@@
银月无声,倾洒沙漠。起伏山丘如同罩上一层寒烟。沙漠之中昼夜温差极大,白昼炎热的温度骤降, 沙漠地表滴水成冰,远处渐渐传来狼群游荡的尖利嗥叫。
这寺庙中的耳房基本被风沙侵蚀掩埋,只有那高高的藏经阁还伫立在夜色中,此刻正亮着不甚明亮的白光。
青鸾只知十年内佛子会飞升,但却不知准确时间,又不敢乱跑错过时机,只能在这破庙中住了下来。好在还有这树精陪伴不算寂寞,她除了修炼便是教他看书识字。
她为他取名为优昙,既提醒自己所为何事,也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希望他早日修成正果,去菩萨佛祖的经坛中做个侍者。
“仙子,我今日的字有没有进步?”青年蹲在地上指了指面前密密麻麻的“青鸾”,就像一条满眼期待的小狗,刹那间她仿佛看见他身后有条摇来摇去的尾巴。
少女叹了口气,合上手头的经书,拖了个长音:“有——但下次能不能写点别的?”
她前几日在藏书中找了一本完整的千字经,想带他从头学起,结果他突然犯倔,非要先学她的名字。之后每晚睡前便要写这一大串让她评价,她若是说没进步,他就会在那里蹲着写到天亮。
真是个榆木疙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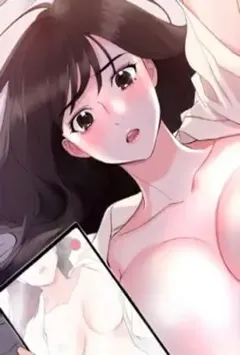





![快穿之大美人在肉文世界[H]最新章节目录 快穿之大美人在肉文世界[H]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776478.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