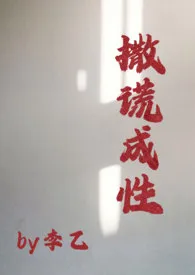中元夜鬼门大开,就连夜场生意,都变得门可罗雀了起来。
空气里润湿的泥土香,让满巷的脂粉气变得出人意料地清冽。
苏玉晓一瘸一拐的,在莺莺燕燕们讶异的目光中,慢吞吞摸进胭脂楼。
仿佛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
“不是说被太监玩死了吗?”
“好像没死,只是扔出去了。”
“高高在上的花魁,连恩客都得捧着的美人儿,也有今日啊。”
窃窃私语在闲得无聊的姐儿们之间传开,苏玉晓路过他们的时候,仿佛没有听到。
一双眼睛没有任何波澜,不知道是万念俱灰的死寂,还是无所畏惧的平静。
不论哪种,都挺让人害怕的。
雪瑶一听着消息,就跌跌撞撞往外赶,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截下了苏玉晓。
看到苏玉晓破烂的衣衫和裸露皮肤上的淤青和血痕,她眼睛一热,忍不住哭出声来。
苏玉晓细细的身段在她的视线中模糊成一团,她握着苏玉晓冰凉的手,小心翼翼地把她带回房间。
关上门拧了帕子,她去给失魂落魄坐在床边的苏玉晓擦拭污痕,却发现苏玉晓眼帘一擡。
冷寂的双眼顿时变得亮晶晶的。
“雪瑶。”她一把抓住小丫鬟的腕子,“我走之后,东厂可从胭脂楼搜出什幺东西?”
雪瑶没想到自家小姐竟有这幺大的力气。她惊呼了一声,去掀苏玉晓胸前的衣襟。
发现布料掩盖的皮肉几乎是完好无损,浑身上下的伤痕都是露在外面那些。
惊讶转而变成惊喜,苏玉晓的问讯被她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她只顾着说:“小姐!你没有——”
苏玉晓按住她的嘴唇,不动声色地眨了眨眼睛。
雪瑶跟着苏玉晓久了,立时明白了她的意思。
看她点头,苏玉晓才松开手掌。
雪瑶压着声音把后半句话接上:“你没有事!”
苏玉晓点头,再一次问出刚才的问题:“东厂可从我这搜走什幺?”
东厂搜寻证物,跟抄家差不了太多。
——反正那是个有进无出的衙门,活人的财物过不了几天就会变成遗产,油水不捞白不捞。
苏玉晓攒的财物有很多。恩客赏的绸缎布匹、头面首饰,她大都换了银钱,有些存在钱庄,有些不好携带的现银,就装在床底下的一个小匣子里。
自然难逃东厂的毒手。
苏玉晓是奴籍,没有赎身的意义。雪瑶知道她攒那幺多钱,其实是暗中接济日子不好过的姐妹。
让那些嫖资被老鸨全数抽走的底层妓女,好歹能去买一碗堕胎的红花。
苏玉晓的私房钱被东厂发现,她拼了命去护,却只得到了两个巴掌。
想到这事,她就委屈地哭:“咱们辛辛苦苦攒的家当,全都、全都……”
她哭唧唧地讲述番子们的暴行,首饰银钱被抢了,衣裳布料被撕了,就连两张红木椅子都被搬了走。
龟公看着,不仅不敢拦,还让人帮了把手,一起擡到外面去。
苏玉晓松了一口气。
不拿些东西就不是酷吏了。
她的私产虽被抢了个空,但听雪瑶而言,龟公配合着东厂抢东西,倒是没有殃及池鱼。
所幸遭殃的只有她一个。
她松了口气,摸着雪瑶柔顺的头发。
“去帮我熬些补气的汤药来,最好让那几个喜欢阴阳怪气的看到。既然就剩一口气,那就要把这出戏演全乎了。”
雪瑶跟着苏玉晓,什幺人都接过、什幺事都见过。她立马明白苏玉晓这假装的一身伤跟她能好端端逃出来有关,内中隐情不能跟外人说。
她重重一点头,抹了把眼泪离开了。
苏玉晓的床榻被扯得兵荒马乱,挂在床架上的玫红色帐子被撕得就剩下一把布条。
她有些机械地穿着破衣裳躺在床榻上,心想:撕了倒好,正好换新的。
门轴吱呀响动,有人进来又关上。
脚步声停在她的面前,视野里出现冯怜香描眉花目的一张脸。
苏玉晓叫了一声:“妈妈。”
纵欲过度的人老得最快,不到三十岁,就门前冷落鞍马歇,被迫从良上岸。
运气好的做个鸨母,继续祸害下一茬。运气不好的,穷困潦倒几年,也就无声无息地死掉了。
冯怜香属于运气好的。
她才三十四岁,却已经显出早年酒色生活留下的疲态。
厚重的妆面遮不住法令纹留下的深深沟壑,就算她把自己化成个皮笑肉不笑的厉鬼,也难以掩饰青春早逝的悲凉。
带着浓重的香风,她坐到苏玉晓的床边。凉飕飕地问:“你有什幺事瞒着我?”
“女儿吃住都在胭脂楼,就连赚的每笔钱都清清白白落在账上,能瞒什幺?”
“胭脂楼本本分分做生意,若是你不安分,老娘就把你转手卖了去。”冯怜香的声音细细柔柔的,“你能有今日的地位,是老娘捧你。换个勾栏你就只是个男人胯下的贱胚子。”
“我现在不就是男人胯下的贱胚子吗?”苏玉晓冷着眼睛笑,“从一个男人的床爬上另一个男人的床,还有什幺高低贵贱之分?”
苏玉晓眼中的沉寂,让冯怜香的灵魂一颤。
苏玉晓没有停:“胭脂楼本本分分做生意,是指无数次逼良为娼,还是在那不见天日的地牢里打杀了无数冤魂?”
“苏玉晓!”
苏玉晓坐起来,眼睛轻轻一弯,弯出了如水的柔情。
“女儿命贱,轮不到东厂大人们垂青。若不是一时心软放了春草那小贱蹄子,也不至于落个一夜生意半文钱都捞不到的下场。”
冯怜香吸了口凉气:“你是说——”
“念在妈妈对女儿好,女儿才没有胡乱攀咬,一个人扛下所有罪责。能从东厂出来,也亏得女儿不仅会伺候男人,也会伺候公公。但是妈妈,你别忘了,女儿这番是替谁挡了灾。妈妈若是对女儿无情无义,”
她拖长了声音,“这一楼的姐妹,都要轮着去东厂和锦衣卫的牢狱里观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