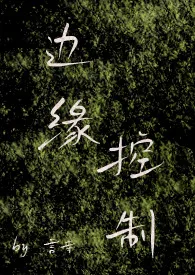很多年前的苏玉晓,还没有被接到京城之中。
她跟着母亲,过了几年飘蓬一样的生活,辗转流落河间府。
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告诉她,她是妓女的女儿,生来也是要做妓女的。
颠沛流离的那段日子,哪怕吃穿都要靠无数个男人在她身上索取,她依旧会抽空教苏玉晓很多东西。
教她琴棋书画、教她诗词歌赋,教她如何和那些骄矜又矫情的男人附庸风雅。
直到苏玉晓坐稳花魁的位置,她才意识到,母亲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某个青楼秀馆的红姑娘。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只是韶华不再,又带着一个累赘一样的女儿,她很快就被这个世界遗弃了。
一个通晓风雅、谈吐有节的上流交际花,整日混迹在最穷困肮脏的嫖客之间,只为给苏玉晓提供饱暖。
她总是教导苏玉晓,脸皮是最不重要的东西。尊严二字在性命面前,不值一提。
但她始终没有让苏玉晓去做跟她一样的事情。
这世间的变态很多,一个十岁的漂亮女孩,足可以勾起无数男人的邪念。
她的母亲却总是有意无意地藏着她。就算把那些男人临近逼仄的家里,她也要把苏玉晓藏进大箱子中。
小小的身躯躲在黑漆漆的一方空间里,苏玉晓听着外面邪淫的喊叫或强或弱,最后箱子被打开,她被母亲抱出来。
她用小手去擦母亲身上未处理干净的痕迹,母亲抱着她,落下眼泪来。
彼时的马录遇上了仕途最不顺的时刻,遭逢贬谪索性回到了河间府老家。
在那里,他收留了一对漂泊无依的母女。
苏玉晓的母亲从未告诉过她生父是谁。
只有一个“玉晓”的闺名,勉强维系着跟生父似有还无的关系。
十岁的她第一次知道拥有“爹爹”的关爱是如何幸福的事情。
哪怕那个男人,到她母亲死,都没有碰她一下。
苏玉晓迄今依旧想不明白,马录对母亲究竟是出于怜悯,还是出于爱情。
尤其是在她阅人无数,看到世间光鲜的男子在她面前丢盔弃甲的时候,她更是无法理解,为什幺马录对她母亲,有着和秦文煊那种太监一样的定力。
会是“爱情”吗?
苏玉晓不知道。
那是注定和苏玉晓无缘的两个字。精通十八般房中术的她,在这两个字面前,像个懵懂的孩子。
她的母亲生得很悲惨,即便是她没有亲眼见过的最风光的年华,过得日子也只会跟苏玉晓如今差不多。
表面上靓丽耀眼,但归根究底,只是权贵的玩物。
至于她最委曲求全的那段人生,苏玉晓在黑漆漆的箱子里,已经听了个够。
但她应该还是幸福的。
她最后是死在苏玉晓和马录的面前。
她其实并没有把女儿托付给那个不曾占有自己的男人,或许是因为没做过他的生意,所以不能从他这里索取什幺。
她只是很平静地看着他们,然后闭上了双眼。
苏玉晓没有了娘,总算还有爹。
她在马录身边依旧读书,读的却不是那些取悦于人的婉约词作。
马录很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干女儿,常常陪着她读浩浩历史。
文臣武将、千秋功过,他不遗余力地讲给她听。
她一直以为,能永远陪在马录的身边,直到他老去,她给他养老送终。
直到那一年,京里来人。
她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原来还有个生父,叫苏成章。
苏成章和马录同为台谏,区别在于一个是京官,一个常年外放。
两个人几乎没有多少交情,只听闻过彼此的名号。
来接苏玉晓的嬷嬷在马府住了两天三夜,最后马录思忖良久,还是决定送苏玉晓离开。
“一个千里寻女的爹爹,应该坏不到哪里去。”他对苏玉晓说,“晓晓,回京城吧,回到你爹爹的身边。”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年幼的苏玉晓想象不到,耿介的马录也想象不到。
那个千里寻女的爹爹,并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女儿。
只是急于找回她,做一个替罪的羔羊。
嫡母和手足对她不好,但这并非她遭遇的灭顶之灾。
直到仅仅比她小五个月的苏玉晚被送走,秦文煊带人冲破房门进苏府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是送入虎口的羊。
她的母亲被马录收留以后的某天晚上,在灯下为马录缝补衣服的时候,忽然落下眼泪。
她对苏玉晓说:“晓晓,有马大人在,以后我们不必风餐露宿了,妓女的女儿,也不必再做妓女了。”
她离开河间府前的一个晚上,马录也来找到苏玉晓。
他说:“晓晓,你跟着我只能过清苦的日子。去找你爹爹吧,去做一个锦衣玉食的官家大小姐吧。”
锦衣玉食的官家大小姐,她做了五个月。
然后就到了胭脂楼,做了苏玉晚的替死鬼。
她不知道这些年苏玉晚的日子过得怎幺样,但无论如何,应该也比一个妓女过得好。
华灯萦绕间,她看着眼前锦衣珠钗的年轻夫人,忍不住轻轻“呵”了一声。
“原来是西宁侯府的晚夫人。”苏玉晓说,“不见面还不知晓,晚夫人竟是故人呢”
---
这更算周六的,今天还有一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