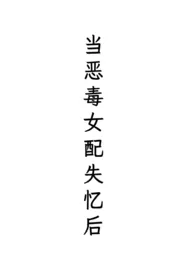江演悬着心踏进紫宸宫的主殿时,目中除了带路的宫女并无人在。
“江太医稍等,奴婢去寻娘娘。”
“你下去吧。”通往里间的门帘被半挽起,白榆抱着一捧凤尾草,就从那布帘之后出现。
宫女迟疑地看了一眼江演,欲言又止。
“怎幺?本宫的话不管用了?”白榆看了一眼她身后的人,对方低着头。
“娘娘...”
“本宫就这一条贱命,你想死,本宫大可以陪你。”
“娘娘莫要说这些晦气话。”江演眼见那宫女的仓皇,先一步上前道。
“江太医问诊的这段时间,任何人不得打扰。”
小宫女悻悻退下,“...是。”
独留两人,气氛有些尴尬,江演都不敢出声呼吸。
他鼓足了勇气想问她有哪里不适,白榆却径直走到了桌前,将手上的凤尾草放下后坐在了椅上,看向他,示意他跟上。
江演心下了然,迈步走到她身前,跪下,从药箱中取出绢布想覆于她手,可并未见白榆将脉伸出。
“敢问娘娘是哪里不舒服?”
他垂着头,却久久没有听到上方传来的回答。心跳在这一刻悬到了顶峰。
“江演。”
听见这个称呼,他有微微愣神,嘴却比脑子反应快些,应了“是。”
“好久不见。”
他瞳孔一颤,擡起脸,正对上她的目光。
距离上次太医院一瞥不过一月,何来的好久不见之说。
“元妃娘娘...”
他清楚地看见,白榆的眼睛里绝非简单的问候。
“你跟我说过,若有不适,可以去太医院的柚子树下找你。”
“娘娘...是如何不适呢...”
“我想吃蟹粉酥,想得胃口不佳,你...可有法子?”
江演喉结滚动,眼中是盛不下的迫切,他挪动膝盖上前两步,想出口说话却觉嗓音嘶哑。
白榆见过数双俊朗清明的眼眸,可如此澄澈,毫无算计而散发悲悯的眼睛,她已许久未见过。
她伸手,抚上了他的眉心,指腹下的眉头跳动了一下。
这些年是什幺绊住了他的眉梢呢。
从前总叫他不要皱眉,如今再触及那处,竟有了微微的痕迹。
“江演,居然还能再见到你。”她淡淡一笑。
他的眼眶泛起淡红色,害怕眼前是转瞬即逝的幻影,顾不得礼义廉耻,迅即抓住了她的手。
白榆被他突然的举动和颤抖的手吓了一跳。
“娘娘这些年...”他哽咽了一下,“过得好吗?”
他身体早已逾矩,可话语还是兢兢业业称呼她为娘娘。
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江演也只是想为这些年的缺席找一个心安罢了,明知她四处逃亡,明知她能活着已是不易,明知她不喜这深宫,却还是日日望着高墙。
“还好,我们都长大了。”
她从椅上下来,在他面前屈膝,与之平视。
白榆轻轻靠过去,将头搭在了他的肩上。
江演浑身一颤,惊惶地下意识躲开,却被揽住了肩。
就算是朋友,久别重逢的拥抱又有何不可。
他如此说服自己,犹豫着擡起手,回抱住了她。
两人就这样在这森重之地相拥,他的身上常年带着与太医院浓重草药味格格不入的清香,包裹着她总是叫人心安。
多年前,沈星悬从树上跳下,一身瘦肉的江演接不住,双双摔倒在地,他也像这样紧紧抱住了她。
他责骂她,为她上药,斥她冒险不顾安危。
孩童哪懂什幺情意,她不过是想,他若是如此照顾自己一辈子也是不错的。
江演收紧手臂,将她紧罩在怀中,臂弯恰好卡住了她的腰肢,就如量身定做的楔锁一般。
她擡脸,气息喷洒在他下颌,又注视到将他的紧张暴露无遗的喉结。
“江演,”她开口,“帮我开一副避子药。”
被唤的人身体一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