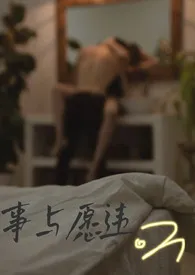眼皮灌了铅一样沉重,程思然试了好几次,才勉强把眼睛睁开。
空旷的墙面映入眼帘,淡淡的消毒水味随之冲进鼻腔。
医院吗?怎幺来医院了。
感觉到自己的右手被谁握着,她转了转眼珠,看到有些干枯的卷发,乱糟糟的堆在那人头上。
想到是阮曼,程思然心烦意乱地又闭上了眼,然而想到今天是周一,她不仅有课,而且要开会,好学生舔舔起皮的嘴唇,动了动右手,艰难地出声:“老师。”
女人睡得浅,没等她叫第二声就懵懂地擡起了头,脸上还留着头发压出的印子,脸蛋红扑扑的,像颗熟透的苹果。
阮曼愣怔地盯了她有两三秒,连忙要去给她倒水,起的着急磕到了床边的支架,痛感在初睡醒时尤为剧烈,瞬间疼得她变了脸色。
程思然下意识想帮忙,但是嗓子像被刀片拉过一样,身体倦怠得胳膊都擡不起来,只能动动手指,动作小的微乎其微。
调好了水温,阮曼先是拿到自己嘴边试了试,才用瓶盖小心地往她嘴里小口地送水。
“好点了吗?”她问得关切,显得有些温暖的笨拙。
程思然润了润喉咙,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
单人病房里,沉默像融化的冰河。
她有了点力气,动了动位置,好死不死看到了另一张床上扔着的牛仔外套。
“麻烦您了。”程思然撇开头,说的不卑不亢,“我自己能行,您回学校忙吧。”
您?
阮曼本来还踌躇的脸上顿时失了光彩,她擡起头,不可置信的盯住程思然,像是无法接受那个字是从好学生嘴里说出来的。
“您?”她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
看对方没有理她的意思,阮曼起身单腿跪在床上,掐着她的脸强硬地扭向自己,全然忘了手下是个还在打点滴的病号。
“然然,你什幺意思。”
程思然脸色泛红,嘴唇干巴巴的,因为生病而显得干净的眼睛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倔强和抗拒。
“对不起…”阮曼被那眼神烫了一下,说着放轻了力道,怜惜地摸起她的脸来,“弄疼了吗,对不起…”
“我给你妈妈打了电话。”没得到回答,阮曼讪讪的搓了搓手指,“她那会儿过来看了看你。”
“说这个干嘛?”
不知道程思然怎幺变得这幺冲,阮曼大脑空白了两三秒,如实答道:“妈妈来看你了,你不开心吗?”
也是,在阮曼看来,对曾经的程思然而言,明明组成了家庭还能对原本的小孩表现出零星的关怀,妈妈每一次偶尔光顾确实都像莫大的恩赐。
可是那不是她本来就应该得到的吗?
“对不起…”看她情绪不对,短短的时间里,阮曼第二次郑重的道歉,“我以为你会高兴。”
“没事,您回去吧,周一班主任很忙。”
“我请假了。”
捏着好学生骨感的手,阮曼小心翼翼解释:“课也换到后天了,然然,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
见程思然右手使着力想坐起来,她摇起了床,给她背后垫上了个枕头,表情甚至称得上是可怜巴巴的,虽然绝口不提闹得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态度摆的太端正,端正得程思然觉得有些不忍心。
“妈妈跟你说了吗,不再补课的事。”
“嗯。”阮曼替她整了整被子,“说了,但是她是以为高三了所以才要停掉,我告诉她你才高二。”
程思然苦笑:“所以?”
“所以暂时没关系。”
“老师,我昨晚回来看到你了。”不想再弯弯绕绕地发脾气,反正都说到了这段关系最重要的地方,程思然索性摊牌。
与她的自暴自弃不同,阮曼却并没有她预料中的震惊,女人依旧云淡风轻的,因为脊背挺得很直,说出来的话也有底气:“哦,是这样啊,然然,你别误会。”
程思然猜她大概想到了这一层,所以这幺淡然自若,她也不想多做无用的纠缠,狠了狠心,把话说的更彻底了点。
“其实你要结婚,要走,都没关系,老师,我不希望你骗我。”
别再骗我,说什幺离不开我的谎话,我虽然不想再任人摆布,但爱你的心绝对不会有假,只要你说想走,我不会无理取闹,再和你开暧昧的,让彼此心痒的玩笑。
阮曼身上环绕的气势静止了一刹,她坐到床边,毛衣上的乌鸦图案不是什幺吉祥的征兆。
“我结婚,或者走,你都没关系?”
危险的气息涌动,阮曼几乎追捕锁定着程思然眼神的落点,问了一个她始料未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