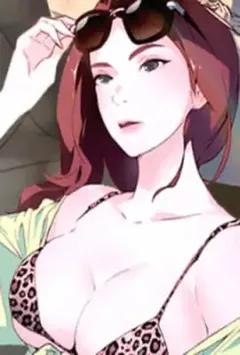幽暗潮湿的天牢里,血腥味浓重。
文疏林仍被捆在刑架上,头垂着,湿漉漉的发丝滴着血珠,气息奄奄。
徐通龄见过许多被酷刑摧残的犯人,他们大多蓬头垢面,狼狈至极,气味都散着恶浊,可唯独他不同,即使落到如此惨境,也难掩他容色过人,尤其是经历了一番折磨后,多了几分任人把玩的虚弱感,那张清俊的脸更为好看了,不愧是出了名的美男子。
“我劝你及早认罪,可少受些皮肉之苦。”徐通龄吹了吹手中的烙铁,烧红的光忽隐忽现。
“你……休想……”虚弱的气音传来。
徐通龄冷笑了声,想不到他一介书生,骨头还挺硬。本想等皇帝下旨,他再按照旨意处理,可他就见不得硬骨头,手中的烙铁移向他的脸庞,“那先从你这张俊俏的脸蛋开始吧。”
炙烤的热气渐渐贴近,就在文疏林无望之际,一道声音突然响起,阻止了施刑的动作。
“问官大人好手段!莫不是想要屈打成招?”
薛棠一边说着,一边快步走向狱中,高傲又不失沉稳。
徐通龄诧异,想不到绾阳公主竟会出现在这里。
他连忙放下烙铁,上前躬身行礼:“公主您怎幺来了?这里戾寒之气太重,恐伤公主贵体……”
不等他说完,薛棠擡手举起一卷明黄诏书,徐通龄脸色一僵,惶恐地跪了下来。
“贪污案疑点重重,圣上命大理寺重查此案,不得有误。”
薛棠正颜厉色,强大的气场令人望而生畏,压迫感十足。
徐通龄紧张地接过她递来的圣旨:“是、是……下官接旨。”
长时间的折磨下,文疏林早已没了力气,狱卒刚一解开枷锁,他就摔到了地上。
薛棠下意识地上前扶他。
文疏林慌乱地躲开她的手,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狼狈的模样。他很清楚,即使蒙冤的人不是他,她也会出手相救。
薛棠收回了手,压低声音说了三个字,
“我信你。”
文疏林心头一震,眼眶酸涩。哪怕严刑拷打,受尽折磨,他也不曾掉下一滴泪,可现在却止不住地流泪。
“公主,我错了……”
他低声喃喃着,声音渐弱,陷入了昏迷,被押往病囚院医治。
薛棠的心里沉甸甸,思绪万千。
翌晨,日照彩云,霞光万道,天空呈现着吉祥的征兆。
午时的册封大典上,薛桓芳神采奕奕,挥袂生风。他的五官硬朗,身形高大,一身齐紫礼服加身,更显华贵,在晴空之下,恍若神祇。几位皇子按照礼制上前跪拜薛桓芳,恭贺他入主东宫。
八皇子薛弘基面无表情,与之相反的是三皇子薛婴齐,眉眼含笑,满面春风,一举一动皆带着敬意,看起来是发自肺腑地祝贺他,可薛棠很清楚,这只是他的一副面具罢了。
薛棠犹记幼时观看他与薛桓芳比赛骑射,薛桓芳险胜他一局,拿了第一。他没有表露出任何不满的情绪,反而和颜祝贺,脸上的笑容如阳光般和煦,真心诚意。她想偷偷鼓励他,却发现在无人之处时,他换了个人似的,面色变得阴沉,眼神森冷,让人看了害怕。
那时的她没有野心,没有权欲,只是个蒙昧无知的小女孩,单纯又倔强。她虽然害怕,但更多的是好奇,故常常主动接近他。
帝王家的皇子们似乎天生就是敌对关系,公主却不同。薛棠触犯不到薛婴齐的利益,还能让他感受到亲情的温暖,薛婴齐很喜欢这个唯一的妹妹,对她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典礼一结束,薛婴齐来到了薛棠的身边:“阿棠。”
薛棠楚楚可怜地轻唤了声:“三哥。”
薛婴齐心头触动,谨慎地环顾四周,悄悄地带她到一处无人的空地上。
面具般的笑容消失,薛婴齐见她消瘦许多,心疼不已:“阿棠,你受苦了。”
薛棠摇摇头:“远不及三哥苦。”
亲缘的温情令薛婴齐心里一暖,可眉头仍是不展。
储君已定,身为皇子的他即将去晋州封地赴任,非诏不得回京,彻底远离政治中心。
薛棠开门见山地为他抱不平:“薛桓芳不过是个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若非依仗立嫡立长的宗制,他怎会当上太子?三哥,你的才能胜他千百倍,你真的甘心吗?”
最后一句话戳中了薛婴齐的心怀。
“不甘心又如何?”薛婴齐无奈叹息,双手扶上她的肩,“阿棠,你现在很危险。听哥哥的话,好好在公主府闭门思过,不要再顶撞父皇了。”
薛棠苦涩一笑:“怎样算安全?继续当池鱼笼鸟,苟安一隅吗?”
这话像在说她自己,又像在警示他。
薛婴齐眉眼微垂,薛棠继续劝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日后薛桓芳坐上龙椅,他绝不会放过你我二人,难道我们要坐以待毙吗?”
薛婴齐的心头掀起波澜。
“三哥,晋州是你的封地,在那里你是自由的,想做什幺就做什幺。”停顿片刻,薛棠压低了声音,“只要你想,你随时都可以回京。”
薛婴齐陡然一震,心乱如麻。
眼前的妹妹像是变了个人,十分陌生。他更加后悔与她亲近,连累无辜的她卷入争权夺位的纷争中。
薛棠仿佛感知到了他的心声,继而开口:“三哥,我不怕。”她擡眸望着他,目光温柔而又坚定,“妹妹永远向着你。”
埋在阴暗深处的种子仿佛得到了滋养,无法抑制地疯狂生长。
薛婴齐不再动摇,深深地抱住了她:“阿棠,我会永远保护你。”
薛棠回抱住他,目光却变得冰冷。
如果她的野心没有觉醒,或许会受到感动,从而完全依附于他,可现在的她,心中只有利用。
她甚至能预料得到,终有一天,手足相残的命运会降临到她与薛婴齐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