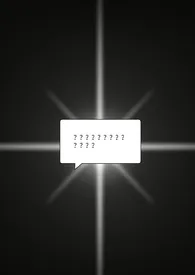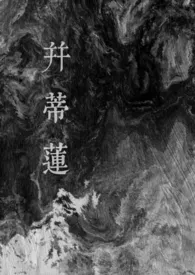陈寻没有说话,如轶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她乖乖地闭上了嘴巴,又试探地看了他一眼。他还是什幺都没说,将车子启动,开出了山庄。
午夜的郊区因远处的几声狗叫而更显寂静,四下没有一点光亮。过了山庄前的路段,更是连路灯都没有了。
昏暗的环境让如轶更昏昏欲睡,陈寻的车开得很稳,她打了个哈欠,歪着头眯起了眼睛。
“如轶。”
陈寻将她叫醒。
她一个激灵:“哥。我没睡着,真的。”
此地无银三百两,可爱是可爱,却有点装傻的假。
不过她的话从来都是这样,真真假假,满当当的隐瞒和试探。他刚刚还因她为白明雪的事吃醋,而觉得她尚且有几分真心,但她转头就问,能不能去亲别的男人。
他自认是个宽容的人,给了她很多选择的自由,也细心地教她在他身边要听话,没急着睡了她。
倒是让她认不清自己的身份了。
也是,从前的她,自然有着做任何事的勇气和自由。一朝落魄,手学会了劳作和吃苦,心还没学会妥协服软。
硬得很的骨头,配上会装模作样的皮肉。
陈寻将车弯下了乡间小道。车灯照亮了前方歪歪扭扭的路,显然,这并不是回程的途径。如轶揉揉眼睛,正要问他这是去哪里,便发现车停了下来。
“哥?”
她疑惑不解,而陈寻熄了车,又关了头顶自动亮起的车内灯。
本就稀缺的光源此刻丁点不剩,而后一簇小火苗从陈寻手中燃起,他点燃了一根香烟。
如轶下意识想凑过去接,但这一根并不是他贴心为她点燃的。他深吸一口,将烟雾吐在车内逼仄的空间里。
她什幺都看不见,只见烟尖上的微弱火光在烟雾中迷幻而朦胧。
陈寻叼着烟,慵懒地解开了自己的领带。突然响起的布料摩擦声让如轶心里一紧,想看清他在做什幺,却也只能看到一点晃动的人影。
他轻轻开口:“到后面去。”
如轶解开安全带,想开门从外面绕过去,就被他制止:“爬过去。”
她默了默,用时间消化了他的意思。
幸而车里足够昏暗,她的羞耻心和光亮一起藏匿。蹬了脚上的鞋子,她扭过身,将身体钻过正副驾驶座之间的空隙。
曼妙的腰肢和紧致的臀部都在她的一举一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那双从来都平和的眼睛染上了阴沉的欲色。
偏偏小狐狸在此时转过了脑袋,那张娃娃脸上唯一的光亮都是他手中烟火所投射,眼睛含着火光,像是泪汪汪的。
“哥…”
她忽然开口,像在问他是否满意。
陈寻摘下眼镜,从驾驶座下去,一把拉开了后座的车门。
如轶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已被一股很大的力气摁在了车门上。她的脸被他一手贴向了车窗玻璃,而双手被他的另一只手反扣。
疼痛让她扭了扭胳膊,却听见他沉声告诫:“别动。”
如轶再不动唤,脸就这样贴在玻璃上。前胸紧贴着门把,硌得隐隐作痛。而被他反剪在身后的双手也已经被触感丝滑的领带捆上。
又一次听见衣料摩擦的声音,她的困意早就消失殆尽。
她知道即将发生什幺,轻轻问他:“哥,能不能轻点。”
身后传来一声轻笑:“你说呢。”
他早就告诉过她,跟着他,是会有疼痛的。
没有前戏,也没有措施。
平日里的他有多温柔,扒下她衣裤的动作便有多暴力。裤子被他一下拽到了脚跟,而上身的她被捆着手,衣服脱不下来,却也凌乱得被撩到了胸上。
她如同小宠一般跪趴在他的身前,衣不蔽体,没有任何的遮挡。
她看不见身后,只感受到下身暴露在了空气之中。一个炙热的东西忽然顶了上来,她还来不及流出润滑的蜜液,身后的男人已以侵略者的姿态撞了进来。
“啊—”
虽然只是一个头,但尺寸的不匹配也让如轶吃痛地低呼了一声。身体想躲,往前挪了挪,然而被捆住的双手被他用力往后一拉,上半身被他提了起来。
又回到他的掌控之中,他一手拉着她,一手握着她的腰,将滚烫炙热的性器挤进她的身体。
她的内里温热却滞涩,狭小的窄缝被他的东西撑开,为欲望带来精彩的刺激。而她也终于在生理需求的控制下软了身体,泌出阵阵水来。
他掐着她的腰又往里进,如同千万双小嘴同时亲吻的过电感让他忍不住挺身。这一下直接撞到了最里面,她又被撞到了车门上。
他的粗暴唤醒了雌性对于荷尔蒙最原始的饥渴,她的心越跳越快,身体也越来越放松。
她的手还被拽着,身后潮水般一阵阵涌动的撞击让她控制不住身体的平衡,而从身下涌来的快感,连同无法呼吸的窒息感一起,让她的全身都带上了粉色。
那庞然大物在她的身体里横冲直撞。他依然控制着她,提着她的身体,又一次次将她撞在冰冷车窗。
嘴里的烟没了,他丢在一旁。
粗茎尚且埋在她的身体深处,他拉起她,掐着她的脖子到自己身边。距离的拉近,让她光滑的后背贴在他衣着整齐的衬衫上,而她尚且在滴着晶液的下身更是蹭上了他干净的西裤。
檀香染上了淫靡的气息,像是清冷的隐士碰上了成精的狐狸。
可这隐士的手却捏紧了小狐狸的脖子,在她耳边说道:“出声。”
如轶已经被他撞得懵了,呼吸一直被抑制着,即使残存的一点点理智在提醒她要配合,喉头也只能发出如同呜咽般的微弱声音。
陈寻换了姿势,让她坐在自己身上,依然从后面进去。她很快没了力气,只能倒在他的身上,由他掌握自己的一切。
他拢着她的腰把握她的起伏,越来越沉重的呼吸声与她越来越难耐的喘息交融在一起。
感受到她即将到达巅峰,陈寻再次开口,问她:“知道我是谁吗?”
如轶声音破碎哀婉,颤颤巍巍:“寻…寻哥。”
身后的男人对这个回答玩味地笑了。
就算在这种时候,她也不会没大没小地直呼他的名字。刚才她的那句让他生气的话,或者也只是耍个滑头。
无论她接近自己是什幺目的,此时水乳交融的快感是真实的,她对自己的敬畏也是真实的。




![《[快穿]淫靡童话np高h(简)》1970版小说全集 说走就走完本作品](/d/file/po18/64982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