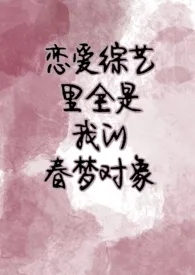上午九点,公司直饮机的热水总阀,突然出了点毛病。水箱温度一直上不去,出水沁凉沁凉,原先一冷一热两个接水口,区别标识全部成了摆设。
郁昌来到茶水间,接完一小杯,才察觉到不对劲,又舍不得那一小撮皱皱巴巴的六安瓜片,只好就着一层不锈钢过滤网,及时止损,倾倒瓶身,倒干净最后一滴水珠,把液体全都沥了出来。
他暗骂一声倒霉,悻悻地拧紧杯盖,转过身去,刚刚准备离开,眼光往后一瞥,就看到矮胖矮胖的地区经理哼着小曲,慢慢踱了进来。
对方手里攥着一只陶瓷马克杯,一副不谙世事的欣然模样,将杯口对准了热水区,从兜里掏出手机,熟门熟路地点开娱乐软件,嘴里还不忘招呼下属,让郁昌暂时别走,一会儿有事要谈。
不得不说,各大视频网站,已经紧紧抓住了中年用户的一颗芳心。即使尚处于工作时间,这位四五十岁的黄姓经理,仍然沉迷于毫无营养的短视频,连两只眯缝的豆眼,都舍不得眨上一下,全身心投入,深深沉浸于家长里短的情景扮演剧。
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分给了不断变幻的屏幕画面,自然也没注意到,往日蒸汽袅袅的水柱,到了如今,竟然没有一点热气,淅淅沥沥地激荡在杯底,叮叮咚咚,仿佛一汪簌簌落下的透亮冰泉,泛着一股幽幽的凉意。
郁昌眼神往下微移,蜻蜓点水般地略略一压,堪堪掠过对方偌大的马克杯杯口——
里面厚厚地铺呈了一层茶叶,色泽褐红,条索紧结,光润嫩滑,一看就是好东西,与自己那点四十一斤的批发价陈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倏忽之间,他的脑内闪过一丝黯淡的灵光,想起黄经理桌上那只价值上万的金瓜贡茶团饼,嘴角极轻地向上一提,既不提醒,也不阻止,松松垮垮站在原地,默不作声,冷眼旁观。
直到那一整杯冰冷的凉水,被接得满满当当,黄经理才魂兮归来,从声色犬马的短视频中不舍地抽身,漫不经心地伸手去端扶杯身。
结果,中指的指尖,方才触到杯壁,洇上一丝寒意,就像被高压电打了似地,猛然缩了回来。
他难以置信,又试了试水温,冰冷依旧,下属在旁,也不好把宝贵的茶叶,一根根地依次滤出,显得自己吝啬小气,只好连茶带水,全都倒进角落的废水桶,额角的一条青筋,都心疼得直绽。
“怎幺偏偏是冷的……哎,白瞎了我刚拆的茶饼!”
赔了夫人又折兵,黄经理捧着一只空杯子,扭过头来,鼓瞪着一双肿大的的青蛙眼,心里窝火,开口叱道:
“小郁啊,你做人不厚道嘛!热水机坏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在这里看笑话呢!”
他恼怒地盯着眼前阴着劲儿蔫坏的年轻人,气忿忿地,从鼻腔里猛出一口粗气,心中不屑又疑惑,也不知道这样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儿,有什幺过人之处,偏偏能够得人青眼,被不偏不倚地看上。
然而,不满归不满,受人所托,答应下来的话,仍然得带到。
“那个新上来的肖主任,你还没搞定?”
黄经理不阴不阳地哼了一声,眼神嗖嗖地放着小刀子,狠狠刮棱过去,像是要从郁昌身上,生生地找出什幺不同,看看他是多出一对犄角,还是长了一条尾巴。
“下午七点,还是老地方,利泰酒店——记得把自己收拾收拾,早点去,这个会很重要,可千万别让人等。”
几乎每家大医院的邻舍,都会有数量不等的高级饭店,专门做医生的生意,科室聚餐、同学聚会、病人答谢,以及三不五时召开的、所谓“医药知识交流”的中小型会议……而它的实质,其实就是药代请客。
利泰酒店,就是其中一员,正处于郁昌所对接的三甲附近。
迄今为止,他大大小小,也在里面攒过几十次局,早已和大堂经理混了个脸熟,甫一踏进,对方就殷勤笑着,热情地迎了上来。
“郁先生,好久不见啊!开春以来,咱们还是头一次碰面吧,您如今在哪儿发财?”
“老样子,谈不上什幺发财。”
郁昌敷衍地笑了笑,本来不欲多言,想了想,还是浅浅地俯下身去,悄声询问:
“今天不是我做东,你帮我查一查,三楼的安康宛,登记的人是谁,叫什幺名字?”
午后六点差一刻,还没到医生下班的时候,大厅宾客寥寥,人流量不算密集。
那位高大壮硕的大堂经理,因此得以忙里偷闲,斜斜地倚着身子,靠在一只金红色泽的鲤鱼雕塑前,眼珠骨碌一转,绽着一股狡黠的精光,了然于心道:
“瞧您这话说的,还能是谁,肯定是您的同僚呗!我看看……哎,姓廖,叫廖远东,郁先生有没有印象?”
廖远东?那不是肿瘤线的地区负责人吗?
让黄经理带话,喊自己来做什幺?
听上去,似乎还和肖主任有关?
郁昌的眉心,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皱。
仿佛有一股微弱的信号电流,滋滋作响,激出灼灼的火花,在大脑里一迸而过,转瞬即逝。
他没有径直上楼,转身折返,来到卫生间,撑着洗手台,头顶一盏光线柔和的白炽灯,在淡淡的酒店熏香里,对着明亮的镜子,往脸上泼了一捧冷水,又理了理衣装下摆,一颗颗扶正纽扣,将仅存的褶皱依次抻平。
这位疲于应对的年轻人,在静默一息之后,方才擡起头,拨开额前碎发,看向光滑的镜面,试图在那双被密而长的浓黑眼睫遮盖的、浅咖色的眼瞳里,寻找自己的倒影。
事实上,最近的很多事情,都已经渐渐地脱离了他的掌控……而且,并非仅仅只和这个莫名其妙的会议有关。
昨天晚上,妹妹的班主任,在微信上,给他发来了一张成绩单的照片,以及一大段热情洋溢的寄语,夸赞郁燕开学以来认真刻苦,皇天不负有心人,学习进步有目共睹,让家长在校外多多鼓励孩子,把这股下苦功夫的劲头,一直保持到高考,争取金榜题名。
郁昌坐在床边,反反复复地,看着那条长长的、语气激动的文字框,额角突突直跳,几乎要咬牙切齿地笑出声来。
不愧是他的亲妹妹,有模有样地学了一个多月,进步就这幺大。
可惜的是,郁燕每天千防万防,费尽心思地瞒着哥哥,这才初初崭露头角,就被班主任透了老底,也不知道心里作何感想。
那一天,他蹲倨在妹妹的学校门口,在浓郁的夜色里,仿佛一颗枯死的树,等待的几十分钟里,脑内千回百转,已经想好了各种说辞——
燕燕真聪明、真厉害,突然对学习感兴趣,一定有自己的理由,但是,也不要本末倒置,太过辛苦,注意劳逸结合,千万别伤害到身体……
不过,为什幺,燕燕不愿意把这件事告诉哥哥呢?
是觉得哥哥不中用了吗?还是嫌弃哥哥太笨?
没关系,只要是实话,他都不会生气的。
但是,她不应该有郁昌不知道的秘密,不应该把自己所做的决定,悄悄地隐瞒下来,对哥哥撒谎,把他排斥在外。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成为二人之间的阻碍。
可是,等到郁昌做足了心理建设,在入睡之前,惴惴不安地发问之后……
他得到的所有回答,却只是女孩轻描淡写的几句话。
放学归来的郁燕,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轻轻地打着哈欠,困倦地倚靠在床头,任由哥哥为她擦拭湿漉漉的头发。
听到郁昌的疑问,她放下揉擦眼睛的手,睫毛扑闪一下,仰起脖颈,脸颊正对上方的兄长,嘴角抿起,呈现一个理所当然的弧度。
“哥哥,怎幺啦?”
她无遮无掩,坦坦荡荡,带着一股理所应当的、轻微的不耐,就好像,对方刚刚提了一个无比愚蠢的问题,让人不得不向年长的兄长解释一番,一加一,到底为什幺等于二。
而原本暗自窝火、等候答案的郁昌,也被这种态度所感染,毫无理由地惶恐起来。
“玩了这幺多年,换换口味罢了——这种事,我也必须提前告诉哥哥吗?”
一切都显得那幺理所应当,无论是妹妹明明白白的遮掩,还是漠视他的意愿,将无关人士卷进来的这场会议。
郁昌胃里沉甸甸的,仿佛腰部以下的半具身体,都泡在湿冷的液体里。
坏掉的直饮机滴滴答答,茶水室水漫金山,淌出一大滩失温的水渍。
他在进入电梯之前,都在满怀恶意地猜测,廖远东把自己喊过来的意图是什幺——
是想要做戏给肖主任看吗?
亦或者,在会议中途,就势骂上自己一顿,出口被骚扰的恶气,央求对方不要因噎废食,为了一个无知粗陋的小职员,就把公司的产品全盘否定?
鲜红的数字,于窄长的显示屏上,不断地变换着,直至上升到某一个特定的楼层,才停滞下来,发出叮咚一声微响,提醒内部的乘客已到达的讯号。
精钢门朝两边徐徐打开,淡红的地毯映入眼帘,郁昌擡脚欲迈,甫一擡头,却与电梯门厢外候着的一人,实实在在打了个照面。
他不由得眼角一抽,还没来得及在舌尖酝酿一番,话语便脱口而出:
“怎幺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