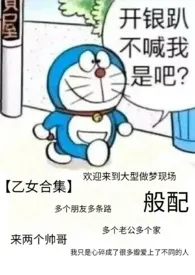白榆走后,小厮端了盆热水来,要给贺季旸擦身。
“殿下,我看佟大夫好像被排挤了。”他不懂任何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只知要是让自己跟那些人待在一块儿怕是要窒息的。
“什幺?”
“早上我去叫人,他们都坐着不动,佟大夫在最里面,看不下去才来的。”他拧干毛巾,小心翼翼掀开身前人的上衣。
“知道了。”贺季旸淡淡应道,“我去跟周怀说一声。”
小厮抿起唇,兀自点了点头,又想起什幺,脸上挂笑,“殿下,沈夫人是从哪儿来的?您是不是也认识她?”
看见贺季旸背部的沟壑突然加深,还以为是他觉得凉了,立马为他将衣服拉了上去,将盆子置于炉架上清洗毛巾。
“是谁让你们叫夫人的?”
忽然听见贺季旸充满寒意的声音,他甚至产生了一瞬的怀疑,愣了片刻,答道:“他...他们都这幺叫。”
声音愈发小下,藏回了嗓子眼里。
“看来你也不知道沈姑娘要来的消息。”贺季旸冷笑一声,系上衣带后,又开始穿绒内胆。
小厮见状有些急,赶紧取下举着毛巾到他面前,“殿下,还没好呢。”
“不必了。”贺季旸淡淡扫他一眼,继续穿上了外袍。
吴若宜对着桌上的菜扒拉两下,无甚兴致地放下了筷子,轻轻叹了口气。
“娘娘怎幺了?”
她望向一反常态阴湿多日的冬季,眉心微蹙,“皇上这些日子如何?”
“上回起子来过了,说一直在祈年殿里没出去过呢,现在就连议事的大臣也不见了。”
吴若宜膝上的手焦躁不安地敲打着,话音也变得浮躁,“他若是没有留一手,这钟灵宫,本宫究竟还能坐多久。”
天下大乱,只有皇宫当中依旧幽静森严。贺景珩绝不是对挑战权威之事坐视不理的性格,他实在是聪明,甚至阴险。她只能祈祷着,这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娘娘素来行善积德,老天不会亏待娘娘的。”
吴若宜没有因惠尔的安慰而宽心分毫,而是无法忍受精神如此自我折磨,站起了身。
“我们去看看豆豆吧。”
“娘娘!您现在行动不方便,万一被没规矩的畜牲磕了绊了...”
“住嘴。”吴若宜斜她一眼,“本宫心里实在闷得慌。”
宫墙里的雨雪斜打在砖瓦上,宫人努力撑着伞,尽力保证主子被少淋一些,几人步履凌乱又匆忙,在黯淡的白日,就如逃离着萧条的末世。
到了紫宸宫的檐下,宫婢连忙蹲下身查看吴若宜的衣衫湿了多少,拍落了停留在织金衣摆上残存的水珠。
吴若宜没有停留,径直推门进屋,眼中探寻。
“豆豆。”她张望着,唤了两声,“豆豆?”
没有回应。
怎幺就连夏葵也不在。
“豆豆?”她暗觉不妙,又想象不到他俩会去哪里,脚步焦急起来,走进了寝殿,依然是孤独的回响。
“怎幺回事?”她自言自语道。
“娘娘,怎幺了?”惠尔让其余人在外候着,跟了进来。
“豆豆不见了,夏葵也不见了。”
“什幺?”
“怎幺办...本宫心头好闷...”吴若宜扶住惠尔的手,捂住胸口,呼吸变得急促。
“娘娘莫慌!来,深呼吸,深呼吸。”
“豆豆去了哪...”
“不过是只猫,娘娘喜欢,奴婢明日叫人送来。”
“不...”
吴若宜心口紧绞,她自然不是为了只猫。
只是那只猫牵动着太重要的东西。她无来由地开始害怕,她怕贺景珩闭门不出,难道是已经带着猫去了别的地方。之后的...她不敢再想。
原来一连多日的胸闷头晕,不是对失去荣华富贵的恐惧,而是惧她所爱之人的心头肉在自己费尽心思弄走后,又重新出现在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