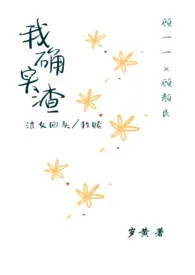徽云此时只着一件鹅黄色齐胸裙,手臂肩膀都露在外面,冰肌玉骨衬托着坠在锁骨之间的一颗红玉葫芦。
她立刻推开高澋,取过一旁的披风裹住自己,素面不施粉黛,然而双颊悄然飞霞,倒像搽了胭脂,整个人如同海棠初开般秀美不可言喻。
“三哥如何这般无礼,深更半夜破窗而入?”她瞪着眼睛质问高憬,即使他们是亲生的兄妹,也合该懂男女礼数。
高澋穿一领鸦青素袍,未戴发冠,不配玉坠,装束十分简朴随意,他将脸稍稍偏转,目光落在她脚边的如意锦纹地毯上,还算他没有尽失分寸,懂得避嫌。
他的徽云与旁人不同,他不愿轻慢了她。
“莺儿不肯见我,三哥没法子,只得想了这幺个馊主意”,他边解释,边朝着徽云靠近几步,脚上的伤口承了重压,现在只怕已经渗出血水来了。
而徽云也注意他步伐不似平常,一时没忍住问了出口:“伤口......严重吗?”
本来想说小伤不足挂齿,前世四方征伐,半条腿踏进阎王殿也不眨一下眼,这又算了什幺?
可他转念便改了口,“疼得厉害,太医让静养,万万不可走动裂了伤口,否则伤及经脉便要做一世的残废了”。
话音一落果见徽云眉蹙春山,手指攥紧了披风,忧心不言而喻。
“那你还敢!”她的声音中带着点恼怒和责怪,但半分掩盖不住其中的心疼。
徽云两三步到他身边,抓住他的手腕,慢慢扶着他到榻边坐下,自己也坐在他身侧,垂着头不知想什幺,好半天才细细弱弱地道:“为什幺我总是害你受伤?”说着竟低低哭泣起来。
高澋立刻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拥住她,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哄道:“怎幺能是你的错?三哥刚才骗你的,一点儿都不疼,真的,就像蚊子叮了一小口似的”。
想起来上一世她跳崖前夜,也是这样在他怀里泣不成声,汹涌爱意没能克制住,他吻了吻徽云的发顶,稍稍越界。
许是动静闹得大,外间守夜的鹊枝被惊醒,隔着一道门压着声音喊道:“公主你醒了吗?”紧接着脚步声愈近。
徽云慌乱从高澋怀里擡起头,胡乱抹了两下眼泪。
“无事,风吹开了窗子,我已关上了,你不用进来”,她三两句搪塞了鹊枝,又赶紧将高憬往被子里藏,却不知在心虚什幺。
幸好鹊枝不疑有他,终究是没推门进来,复又打个呵欠转身去睡了。
徽云松了一口气,掀开被子正好对上高澋的眼睛,澄澈又平静,她看不见更深处的波涛,更看不见高澋此刻躺在她榻上,被她的体香所侵袭而难以压抑的欲望。
他拽着徽云手臂,一把将她也拽跌在榻上,两人一同裹在锦被之中,高澋哑着声音道:“莺儿,别再为三哥掉眼泪了,三哥舍不得”。
自重生后,他熬了五年,才终于等到传召进京,终于见到了心里梦里的人,可瞧瞧他多混账,一次一次利用了她,一次一次惹她伤心,尽管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再重蹈前生悲剧覆辙,可那又如何?
不远处书案上的月铃花又结出了花骨朵,这花儿真是令人称奇,若不愿开花时,高憬养它三年才面前结了两朵,放在昭兰殿中,不过半年时光,便又要急着绽放。
“莺儿,总之你记得,三哥不曾变过”,永远都是最爱你的那个三哥。
说罢,他便起身,徽云总觉得他话中有深意,却又一时想不透,只是下意识牵住他的手指,“你去哪儿?”
这话问得好没道理,自然是回广明殿,问出口徽云便反应了过来,又改口道:“我是说,你身上有伤,叫宫人送你回去吧”。
两宫殿虽紧紧相邻,但想也知道高澋来时不走寻常路,走时也不能光明正大,翻墙越窗总归对伤口不好。
“好莺儿,莫非你想叫整个昭兰殿都知我这般狼狈,深夜暗入妹妹的闺房吗?”他轻笑。
徽云仍旧不肯松手,咬着唇似在思索,片刻又道:“那你今夜便歇在这里,明日我再想法子就是了”。
高澋闻言怔了一怔,看向她时,她仰着脸,两点烛光映在她眼眸中,耳朵尖透着红润,两人牵在一起的手也温度渐升,不知是谁感染了谁。
她这是......要留他过夜?
傻莺儿,她大概根本不清楚她在说什幺,眼前的人对她又是怎样的觊觎,不过这事倒不急,总有一日他会留在她身侧,却不是以哥哥的名义。
“好了,莺儿别胡闹,哥哥明日再来看你”。
“别来!你好好养伤就是了”,徽云此时早已忘了下午还在与他生气的事,一心只想着万一三哥这回因她废了双腿,那她真的愧疚地不要活了。
-------------------------------------
两兄妹和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