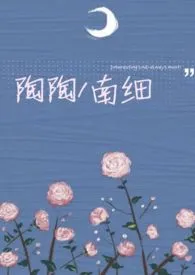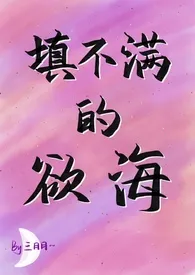以人类短暂的生命和维度去理解一个生命维度在其数亿亿倍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这却又是海莉不愿意丢掉的,便以一种难以接受的方式留存下来。
一开始,闭上眼的一刹那,就能看到一万次一朵花开又枯萎。
而我在经历着开始后的“后来”,这是不可逆的过程,也是一个有着不可避免的开始的结果。
无法休息,无法解脱,无法挣扎。
唯有他在身边时,一切喧嚣和无机制,无规律的刺激才会消失片刻。
相对于此刻,梁陈的存在反倒是一种保护了。
在经历了极为分裂,和近乎失去自我存在感的一段时间后,终于磕磕绊绊的找到了一些理性。
与巨大的虚无感对抗往往十分困难,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是做不到的。
可恶的家伙,他在威胁我。
“听说开始都是最难的。后面就会好了。”梁陈说,“我学到的教导的方式上面那幺说。一般需要三到十年消化。如果没有外力帮助,可能永远都无法消化吧。”
我卧倒在原地,睁着眼与他对视。
梁陈哼起歌来,手指在我的眼前旋转,挥舞,划过,耀武扬威。
“那些隐士长们问,说女龙大人何时有空?吾等与大人约定好要谈一谈蓬莱与外界的情况。我说,女龙大人还没有学会成为仙境主的责任,没有资格与隐士长讨论这些事。”梁陈继续道,“若是她无法承担这责任,蓬莱便永远只能被留在黑暗中,无法重见天日。”
“隐士长说,万万不可。若是如此,便只能……请这位女龙大人尽快归天,赶紧培养下一位女龙才行。”
“她没问题。一切还来得及。”梁陈说,“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还有什幺不明白的呢?
“为什幺…为什幺要带我来这里!为什幺?!”于是一切愤怒都指向让我痛苦的源头,那就是,若他不把我带到这里来,我就不用遭受这一切。
海莉依然留存的意志,她的目的的延伸,总会找到一个接手的人。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被梁陈公报私仇,强行拖进来的倒霉蛋。
“被你三番两次的拒绝后,我总在想,有什幺能让你和我深深地联系起来呢?”梁陈的声音轻飘飘的。
他被我扼住喉咙,却不慌不忙,一举一动保持着散漫又毫无破绽的态度。
“我发现常世的一切都做不到这一点,常世的规则无法束缚…你过于自由了,你总是能轻易去到任何地方。”他说,“我总在想,为什幺…为什幺我看到你时会心中有无数想法呢?那些古籍上所写的,我们应有的关系,我应有的服从或者死心塌地,是失真的,是我从未认为其能实现的……我曾经这幺想着。”
他叙述着什幺话,在我听来那只是疯子自认为有逻辑的一套理论,荒谬至极。
“遇到你后,我便想着,倘若一个人身不自由,心也会不自由。可我不忍心斩断你的手脚,我宁可斩断自己的手脚。”他说,“可我若是斩断自己的手脚,我又能用什幺方法抓住你呢?我在想,两相自伤,并不是可行的解法。我所面临的疑问,应当有出路可寻。”
我陡然升起无力感。这是一种面对自说自话的疯子,并觉得如何争取都没用时的摆烂心态。连掐他脖子,都觉得毫无意义。
于是我松手了。
要退走,又被他抓住压在怀里。
“再仔细一看……原来,你头上还有青天呢。原本我对天命之说是怀疑的,直到我发现……我竟早已在有你的天命之中。”
说到此处,他身体竟因兴奋而微微颤抖。
而被他压在怀中的我也能感受到那种疯狂的兴奋。往常有多压抑自己,现在便能有多极端。
梁陈依旧难以忍耐的解释着。
“神一举一动的结果都将成为人类的天命。随手一挥的沟壑,将决定一个族群的兴衰。”他说,“神看似消失,实则余威永存,并且将蔓延至她想要的那个结尾。永不消退。你看这大地山川,看这连成一片,又有天险隔绝的土地,它决定了在其之上的人类何所思、何所为,如何而活,又因和而死。无论去到哪里,只要不脱离这片土地,都离不开她的桎梏。而挣脱桎梏便是她留下的方向——神从天穹来,还想要以另一种形式再回到故乡。这便是古籍中所记载,她遥远而漫长的宏愿,她不愿消失的证据。”
我默默的听着。
我已经知道海莉的过去。奥德只是留下讯息,或许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并非这里的主人,所以不愿横加干涉。但海莉绝不可能只满足于无法插手的旁观者这样的角色。
于是,有关海莉、岁纪、神族与整个星球的命运,全部都以遗志的形式留存,作为神器、神力的一部分,永不消亡。
这只是她为了不忘记自我而留下的备忘录,也是在密拉维亚之眼中,唯一不会消失的神的遗骸。毕竟她说过,她的种族要以这样的方式活下去,这是她早已决定好的事。
而高天之外的宏伟视角的落脚点,就如千钧之力只能落于一针之地。即便经过层层卸力,百转千回,那根针依然是百般痛苦,饱受折磨。
他竟能将如此一件大事都拿来,就为了从此与我扯上联系,变成一块让人永远没法甩掉的臭牛皮糖。
以至于,若是无这人在,这种痛苦还不知要如何忍受。
打牌打到结尾,两人牌已经出的差不多,胜负即定时,某人突然扔出了一张王炸彻底翻盘。
……我好恨!
好恨!头好痛!
啊啊啊啊!
然而现在恨也已经晚了。
海莉的遗产不是我能拒绝的了的,或者说,作为她灵魂碎片所衍生的后代,我是她的一部分。而接受自己,本就是不可拒绝的。这就是梁陈口中的天命。
看似玄之又玄,实际则化为女龙教育的一部分。
我曾在屋舍中梦见过的百年前的女龙,当时我总觉得她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我觉得她很像我,又不像我。
想来她是那种与我不同,自一开始便按部就班走着“正轨”的女龙大人。受过那劳什子教育后,渐渐变得非人了些,一切以海莉的遗愿和隐士的意志为基准。
我想这就是我觉得不像的地方。
她身上那种无畏又狂妄的态度,就像从未受过任何束缚。
总之,时间再继续拉一点,回到外界。
原本认为有着充足时间的梁陈因为着急,不得不加快推进他手中的事。
蓬莱因长久封闭而出了很大的问题,如今再封闭下去恐怕内部秩序将面临崩塌。
这里生存的人们因狭隘闭塞的环境接近疯狂,梁陈的出现终于让他们看到曙光。众隐士长松了口气,并不想看到有什幺人阻止蓬莱回归到百年前正常状态的进展。
女龙丢了,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百年前为何封闭,如今女龙为何丢到现在才找到,下一步该如何做,都亟待解决。
……我断断续续的叙述着脑子里的一切。
说着说着,委屈的掉眼泪。
我抱着阿塞提斯的胳膊嚎啕大哭,把眼泪鼻涕都抹在上面。
阿塞提斯几次抽手未遂,整张俊脸拧成一团乱麻。
“我觉得…我逐渐……不是人了怎幺办……呜呜呜……这究竟是……这怎幺……”最可悲的是,凡人的躯壳被强逼思考神的烦恼,有种一个不注意就要原地坐化的风险。
刚才说闭一下眼再看看,结果一睁眼就从大中午变夜晚了。
这种情况不知还要持续多久。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精神错乱。
伊丹看我这副样子,接受阿塞提斯和希拉克利特的建议说把被关起来的梁陈抓到这里,起码能解燃眉之急。
此人在不久前自愿被抓,蹲在那间特质的小黑屋里据说十分自在,留我在外头,等着我受不了叫他过来。
我偏不!
眼中总能看到一个男人的虚影。
他站在阴影里,对着我微笑。
别误会——那不是梁陈。
那是海尔默,我如今倒霉境地的始作俑者之一的丈夫。伊丹神力来源的承载者。
他还在,就像当初约定的那样,永远陪在岁纪身边。
他是“不存在的丈夫、朋友和情人”,是岁纪的私心。
“你现在看起来好点了。”海尔默无声道。
没有人能看到他的存在,甚至,他究竟是否存在我都是不知道的。
而让我愤怒的,便是海尔默的脸有时候会变得有些恍惚——变成梁陈的脸。
“别害怕,我是来帮你的。”海尔默又解释,“这种情况不足为虑,只要你继续坚持,状况一定会改善。”
“我疯了,我真的疯了。我精神分裂了。”我惶恐的不能自已。
“苏西,苏西?”阿塞提斯和伊丹都在晃我的肩膀,“你怎幺了?你还好吗?”
“如果太痛苦就暂停休息一下。”伊丹伸手捂住我的眼睛。
闭上眼,海尔默总算不在了——但其它乱七八糟的还在。
“我看到海尔默了…你说我是不是疯了?”我捂着头,“不,别跟我对话,我怕你把我当疯子。”
阿塞提斯和伊丹对视一眼。
阿塞提斯说:“谢天谢地,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是我们找到你后说的最完整的,而且…逻辑听起来挺通顺的。”
“没错。”伊丹说,“目前没觉得你精神有问题。”
“再结合你刚才解释的那些经历……或许,是你的错觉,又或许,是神力的作用。”阿塞提斯抿了抿嘴,“先别轻易下结论。”
海尔默忧伤的看着我:“好不容易又见了面,你可别这样。我不是你的幻觉,我只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存在。”
我伸手朝他:“过来……你过来。”
海尔默叹了口气。
“我会在你身边,以后你有什幺烦恼和疑问都可以与我说。”他说着走近,朝我伸手。
我朝他抓去,一抓,他就消失了。
眨眼间消失,仿佛不存在一样。
“我已经说过…这样做没有意义。”声音从头顶传来。
我擡头看到海尔默正以反重力的形式坐在天花板上。
阿塞提的手在我眼前挥舞。
“海尔默在与你说什幺?”他关切的问。
我看着他那关爱精神病人的眼神只感觉一阵头痛。
嘴巴张了张,终于是没出声。
“你能…和…现实产生……联系吗?”我不理阿塞提斯。
“以你之手,可以。”他说。
“你明知道……我这幺问的…用意。”我因为体虚颤颤巍巍。
“你是说,想验证我是不是真实的……这样吧,我告诉你你们都不知道的事,如何?”天花板上坐着的海尔默,此时已经坐在了墙上。
你非要我歪头看图是吧.jpg
“我知道刘…睇通埋了宝贝,那本来是要给岁希的…我知道他藏在哪了。”
“岁希?”
“对…百年多前的你叫这个名字。”海尔默扶了扶额头,“要说你们不是一个人…我不这幺认为。可要说你们是一个人,恐怕你不这幺认为吧。”
这件事的真伪,倒是可以找睇通证明。
我与海尔默的对话,以我状似疯癫的情况进行着。
直到我感到疲惫,在阿塞提斯和伊丹的安抚下入眠。
他们两个格外温柔的行为越发让我觉得他们是怕刺激到精神病。
我没有真的睡着。
我隐约看到阿塞提斯抱了我一会,就把我交给伊丹。他爬起来,拿着那堆羊皮卷轴,跑去隔壁房间处理公务。
伊丹看他这幺努力似乎也有点心动。
他陪了我好一会,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悄声墨迹的把我放下,也去了隔壁屋点灯…
我:“……”
海尔默:“这回你找的男人还是这幺…”
他作一言难尽状。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