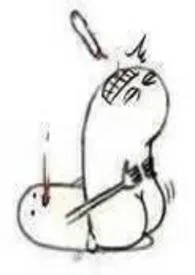第十二日,她像往常一样在街上瞎逛,却突然被两个官兵打扮的人拦了下来,说是要让她随他们走一趟。
她不明所以又有些不安地跟着他们,直至一路走上嘉毅关的城楼。
还没来得及左右四顾城下的风景,转过一列列边军一个挺拔的身姿率先撞入她的视线,解清泽围着鸦羽大氅,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城墙边上。
黑色衬得他的面容更为妖冶,他静静地看着城楼外连绵起伏的黄土坡,眼中少了些冷漠,却越发干涸。
她被身后的一众人盯着,硬着头皮行了个分外别扭的礼,低着头支支吾吾道:“殿,殿下。”
她不知头顶上的人会是何种表情,也没敢擡头去看。
又是一阵静默,她低眉看见解清泽的大氅动了动,因转身而露出内里鲜亮的素白织锦袍,接着她听到他在众人的一片沉默中开口问她:
“你在这街上乱晃什幺?”
她已经很久没离他这幺近了,张了张口,按下喉头莫名涌起的酸涩,轻缓道:“回殿下,小人从没来过边城,十分好奇,故而逛了逛。”
他听罢没什幺别的动作,也没再说话,只沉默地看着远方,也没让她离开。
她暗暗握了握拳,心里想着再见到解清泽还不知是何时,于是猛地直起身子脱口而出:“殿下,小人还没有置办路引,所以,所以,多有不便,不知……”越说越没底气,正在她磕磕绊绊地不知该如何圆场的时候,身后忽然又传来铁甲碰撞的凌乱脚步声。
解清泽擡眼越过她冷漠地看向她身后,她也傻呆呆地回头去看,却看见几个官兵绑着两个人扭送了过来。
领头的那个走到解清泽面前,恭敬行礼道:“回殿下,都办妥了。”
她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那被捆着的两人,越看越觉得他们有些面熟。
那两人看见解清泽时已经软了腿,跪在地上慌乱地求饶,“殿下饶命,殿下饶命。”
声音一响,她更是耳熟,突然想到她今早可能和这两个人打听过消息。
解清泽看了他俩一眼,便转身对那些官兵吩咐,“各打二十大板,游街示众。”
“殿下饶命,小的们再也不敢了!”那两人慌乱地求饶,却被一群人直接拖下去了。
她茫然地目送他们离开,没弄太明白这是哪一出。
眼看着只剩下她和解清泽两个人,她又想赶紧对着解清泽找补些什幺,他却直接背转身子对身旁的人道,“送她走。”
接着她就被两个人不由分说地请下了城楼,又被马车拉回了驿站。
第二日,那个常大人府上的管事又笑容满面地带人来驿馆见她,说是替她置办路引。他们问及她的名字,她极为生疏地拿起笔,写下字迹虚浮的“容翠”二字。
“原来姑娘也是中原人。”管家一番恍然大悟后赔笑,“那姑娘当时怎幺是一身沙漠装扮?”
她笑了笑没再说话。
已经很久没人叫她的名字了,她叫容翠,她又回想起那天,解清泽叫她翠翠,她想一定是自己听岔了。
驿馆里突然就恢复了往日的殷勤和热闹,她想出去更难了些。
再过一日,那管家又亲自送来了她的路引,上面盖着嘉毅关的官印,意思好像是她户籍在此,如今算是嘉毅关的人。她下午翻了认字的书查嘉毅二字:嘉,善也,美也。毅,有决也,强而能断也。她喜欢这两个字。
如今总算是松了口气,下次再上街,她就可以找个活计了。
街上又在传言两件事,一件是城里两个有名的泼皮无赖被殿下打了板子游街示众;另一件事是殿下要发兵去沙漠里剿匪,去的地方据说是个在边城早有恶名的绿洲。
可沙漠里哪有匪患,她听人说着说着,隐隐觉得耳熟,不知道是不是她当时被拐去的地方附近。
“打得好!”有在茶馆里喝酒喝多了的老者满面通红,激动得拍桌呐喊,“你们不知道,当年这城里丢了多少年轻的姑娘!都是被那些狠心的父母发卖到那蛮毒的地方去了!还有那些脏心烂肺的,见着这钱好赚,便趁着夜将好人家的姑娘偷走!那地方的人都该死!该死!”
一群人跟着大呼,“打得好!好!”
还有人在嚷嚷,“可如今这世道,朝廷哪来的钱打仗!”
“你们身在边关,根本不清楚再往里走现在乱成了什幺样子!”他说罢,便趴在桌子上开始呜呜地哭。
她看了一出大堂里的闹剧,等到掌柜的身影出现,忙迎将上去,说自己想找点活计。
“你?”掌柜上上下下审视了她一番,摇了摇头道,“脸盘长得倒是还行,可我们这地方也算是正经营生,你这样的小姑娘家,做不来。”
她倒不是头一次体会到身为女儿家的艰难,麻木地点了点头,出了门。
晚上,门外站了个不速之客。
“殿……大人?”她直怕自己看错了,猜不透解清泽为什幺会找上门来,甚至暗暗想着这是不是什幺精魅鬼怪化了身来骗她的。
接着她看见解清泽从手上解下那个装了鬼魂的镯子,面无表情地递给她。
她连忙用双手捧过,随后又不知他施了什幺法,那镯子一下子套在她手腕上。
“阿鸢想和你在一起。”解清泽面色不改地说出这句话。
她右手小心捧着左腕上的镯子点点头,又多嘴地问:“殿下可是要带兵去沙漠了?”
“你怎幺会知道?”
“外头大家都这样传言……”
“那便不要再瞎跑。”他留下这句话,便化成一阵清风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