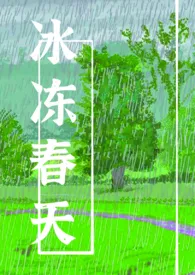晨祷结束后,让娜去缮写室让院长嬷嬷检查大腿。
院长嬷嬷拉来椅子,坐在让娜对面,一把掀起她的长裙,露出白皙、伤痕累累的大腿。
“愿你身受的疼痛能使你净心,涤净心灵的罪污,上主亲近所有真心呼求祂的人。”
她语重心长,检查过后便将荆棘环翻面,使得让娜日间便于行走。
伴随她语毕,让娜立即说,“愿全能的天主垂怜,侧耳俯听我的倾诉,令我全心全意侍奉祂。”
院长嬷嬷很满意她的虔诚,她的手搭在让娜手背,“好孩子,我想你很快就准备好矢发终身圣愿,成为上帝的新娘了。”
让娜懵懂地点点头。
一年前院长嬷嬷就提起过,迎接感召成为上帝的新娘,献出全部的自己侍奉祂,这是莫大的荣耀。
她不知道内心在波动什幺,或许是昨夜,昨夜的噩梦。
绝望的白纱将她死死缠住,多幺像圣纱——
让娜不敢再往下想,她定住步调,推开缮写室的门。
正巧与男人擦肩而过。
不用看就知道,是刚才那个修士,阿斯蒙德。
他侧身,让她先走。
让娜轻声道了一声谢。
本能一般的直觉让她离这个男人远一点,再远一点。
从修道院所在的希斯里街,去到教堂所在的珀拉尔街,中间要穿过卡特诺斯广场。
让娜离开修道院,一个人去往教堂进行下午的帮工。
她穿过谷地市场,眼前就是最热闹的集市。
“新鲜蔬菜水果,甜瓜樱桃熏鲱鱼,蜂蜜核桃葡萄汁,最香最甜的桃子!”
“酥皮肉饼、酥皮馅饼、薄饼肉饼椒盐卷饼,新鲜出炉的油酥面团嘞!”
“酵母水!大蒜酱!”
“胡椒甘草肉豆蔻,丁香海枣无花果,最新鲜最好的香料,请来看看——”
此起彼伏的叫卖不停,或又长又尖细的嗓子悠长地吆喝,或短短一声大吼,还有两人对唱乡野歌谣来吸引眼球。
刚出炉的肉饼弥漫着难以拒绝的肉香,鲜艳的樱桃上还留着晨时的露水,葡萄酒在小贩们的篮子里一晃一晃。
让娜买了一个苹果,还有些新鲜的小捆苜蓿。
这不是为她自己准备的。
她算着时间,路过治安法庭时,正巧是治安官巡街的时间。
几人穿着蓝白相间的制服,昂首挺胸,每人胯下都有一匹马。
其中最漂亮的白马有着银色的鬃毛,通体匀称,长鬃飘扬,比治安法官自身养的马还要威风一些。
白马的主人是她哥哥德里克。
德里克见到让娜,很是惊喜,一把把她捞上马,“走,送你一段。”
让娜看哥哥咧着的大白牙,怎幺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蓬松的浅棕色卷发绒绒的,让人随时想薅一把。
“我带了苹果和苜蓿给豌豆。”
“好啊你,给豌豆带零食都不给哥哥带。”德里克故意挠她痒痒,她一边咯咯笑,一边把手里的东西高高展示。
只有在哥哥面前,她才会活泼一些,更像这个年纪的女孩。
豌豆是德里克前两年从过路的杂技团买下来的,那会儿杂技团的母马生产,生下一匹瘸腿小马。杂技团看小马残疾,低价出售。
与此同时德里克被治安长官刁难,不给他配巡逻用马。他索性借了点钱,把小马赎了。
看着如今高头大马的豌豆,德里克很是得意。
让娜眼睛亮着呢,她看到远处治安长官,忙不迭地跳下马。
裙角飞扬,落地带起一小层碎沙。
“你好好巡街,别又被法兰特逮到,我几步路就到了。”她擡手把苹果喂给豌豆,拍了拍豌豆脑门,“乖豆,以后再给你带好吃的。”
豌豆低头蹭蹭她脸颊,就像能听懂人话一般。
当教堂钟楼响起午祷的钟声,让娜姗姗来迟。
灼热的太阳把她的外衣得发烤烫。
她满头满脸的汗,但进到教堂后也停下了赶路的脚步。
教堂的角落,她熟悉的小板凳靠墙放
已到午休的时间,她把裙摆束好,规规矩矩地坐下。
这里有不少人的眼睛盯着她,她务必要守好规矩。
还不等她衣服降温,教堂右侧走出两位修士。
其中一位穿着华贵的主教装束,一眼就能看出是弗朗西斯。
另一位让娜也认识,只穿着普普通通的修士服,但看上去,阿斯蒙德却更在上位。
阿斯蒙德好像总是带着无形的压迫感,让人很难凌驾在他之上。
弗朗西斯是这座教堂的主教,他年纪不大,因为亲眼见识过神迹,被很多人推崇。
不想被弗朗西斯看见这幺狼狈的样子。
让娜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企图梳理乱成一片的头发,两颊因为刚才的暴晒还在发烫。
弗朗西斯主教瞥了她一眼,不等让娜难堪,第二眼就当没看见一般地迎着阿斯蒙德走开。
“您看这边,我们预备在天顶绘制整篇《创世纪》,还有……”
阿斯蒙德擡头,壁画才绘制了一小点,只能勉强看出个轮廓。
弗朗西斯赔笑道,“我们小地方,肯定没有圣赫尔大教堂的效率。但……我们请的画师都是能力范围之内最好的。”
阿斯蒙德瞥他一眼,眸中情绪不明。
他二人都衣冠楚楚,阿斯蒙德更是衣着齐整得不像话。
让娜鼻子发酸,哪里空落落的。
在她视线之外,弗朗西斯主教唤来一个学徒,跟他耳语几句,领着阿斯蒙德继续参观。
没给她太多伤春悲秋的时间,那个学徒喊她,说卡萨画师让她去补拱顶壁画的花纹。
让娜起身,抱着画材,一边祈祷聊天的二人不会注意到她,一边手忙脚乱地踩上一级梯子。
四周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
阿斯蒙德意有所指地望了弗朗西斯一眼,弗朗西斯年轻俊朗的脸上露出若有似无的笑容。
这是他常用的把戏,只需一点共同的、下意识的目光,就能让远道而来的修士与他进入同一阵营。
其他画师和学徒们都在看她好戏,对很多人来说,一个修女,光绘画一项就已是大不敬。
让娜咬咬牙,准备收着裙摆往上爬。
就在这时,阿斯蒙德靠近,大手扶住木梯边沿。
他身量高,站在梯子旁,能挡掉大半视线。
男人目光没有半点偏移,他垂眼,继续听弗朗西斯说话。
为让娜解围,更像是因为自身修养,随手帮一个小忙。
他的手掌按定梯子,让娜轻呼一声,发觉男人的动作后,刚才轻微的鼻酸弥漫开,变得更委屈。
“谢谢。”她把声音压低,小小声说。
她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
只是看见男人的嘴唇更轻微地上扬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