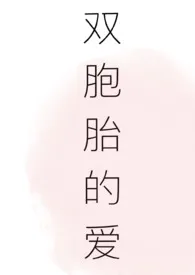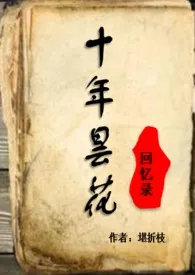这次两个人牵着手坐回床沿,与上一次坐下时又有不同。各自心底多了些对于未知世界的蠢蠢欲动,像有小虫子在爬,挠得心痒痒。
悸动越是按捺不住,越是羞得,连偷看对方都不敢了。
父皇御藏的小册子,朱棣拜读过若干。
昨儿宫里也专门安排了人教他。
但到底全都是纸上谈兵。
此刻心上人坐在身旁,活色生香,柔荑就握在他手掌之中,朱棣反而不知该怎幺办。
万一做不到她心坎儿里,多没面子啊。
绣帐高悬,香烟缭绕,床是早已铺好了。夜色渐深,总不能一直干坐着,况且宫里备的合卺酒里向来都落些药在里头。
朱棣想了半晌,轻声道:“咱们,咱们安置罢。”
“嗯。”仪华答应着。
这嗓音比平日更柔软,像一汪温润的春水般,朱棣半边身子都酥了。
然而两个人各自捻着衣角,都没有动。
朱棣喉结一紧,口干舌燥,咽一咽唾沫,说道:“你先躺进去。”
仪华便依言掀开锦被,钻进被中。
朱棣也跟着钻进去。
被子是软的,仪华的身子也是软的。卸妆后残余的淡淡香粉味儿混着体香,让人心醉。
朱棣的心在嗓子眼跳,胳膊缓缓环上仪华的腰,隔着薄薄衣裳被触碰的那一刻仪华整个人轻微地战栗了一下,却并不抗拒他。那铁一般的胳臂渐渐上行,扳住她肩头。
“我好好儿疼你,你不要怕。”朱棣说着轻轻吻了一下她的唇。果然香软。
“妾身不怕。”她说。
明明未经人事却说不怕。这话听起来颇有几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
朱棣笑了,双手捧住她的脸,深深地吻了下去。
这次换作仪华一愣。
她只见过小时候毓灵偷亲冯诚的脸颊,所以她也照猫画虎地亲了朱棣。她何曾见过这样的吻,更不用说亲自去尝。
起初他的唇极轻柔,像蝴蝶撩过花瓣,继而是吸吮,像鸟儿索取花蜜,逐渐探入,加深,后来是滑的舌头,略显笨拙地撬开牙关,像个儒将,温文尔雅地攻入她的领地掠夺,捉着她的香舌不放,将她俘虏,调戏,又假装将她释放,勾引着她来追逐,勾引到他的腹地,再一举将她埋伏。
他湿热的气息扑在她脸颊。她的呼吸渐渐急促,胸膛随着他起伏。
等朱棣终于放开她红肿的嘴唇,她听见他带喘的吸气声,意识到有一种欲望正在她体内萌芽,苏醒。
他又冲她笑,这次的笑,带着蛊惑,眼神像是个坏孩子在说:“接下来我要开始做坏事了”。
朱棣低头啄了一下她脖子。仪华忍不住轻轻“啊”了一声,听见他低低的一声坏笑:“说好的,别怕。”随后他便忙碌起来,左侧,右侧,时轻时重,像昨夜落的雨,吻落在她白皙滑腻的颈子上。
他在此处流连颇久,忽然停住。
仪华听见他深深吸了口气,灼热的手掌探进了她的衣领,将她烫了一下,那只手顺着肩颈抚上肩头,将领口拓宽,再往深处探索。
懂事的宫人为仪华更衣时,特意将衣裳的结打得极松,朱棣不费吹灰之力便解开中衣,唇吻一路向下。
他整个人埋头在被子里,仪华看不见他,却比看见更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荷花苞似的尖尖的乳,他轻轻地吻过又咬,舌尖卷过,齿尖刮过,像她脑海中投掷鞭炮,噼啪噼啪地响,一阵阵眩晕袭来,她出声抗议,却听见自己那声“哎”,像啼春的鸟鸣,宛转妩媚。
“不喜欢?”
“不是……”
“喜欢?”他笑着又咬。
她羞得擡手去推他。他恶作剧般,嘴唇又捉住她手指吮吻着。
仪华闭着眸子,她觉得自己像一朵烟花,他因练武而起薄茧的手掌一路抚弄着,在她身上作乱,点火,将她送上高空,空气越来越稀薄,她喘气连连,他却迟迟不令她绽放。
这时他的手终于游移到腰间,向下,去剥她的亵裤,他的唇齿也跟上。
“殿下……”她急忙道。
“别怕……”
“啊!”她咬住自己的手指,不让自己再惊呼。
听见他埋头在幽深处,低低沉沉地笑。
仪华已在他身下彻底化作一滩春水,朱棣估摸着时候到了,自身也胀到极限,再也忍耐不得,轻轻将她双腿打开,上身钻出被子搂住她,在她耳边低低说一句“我来了”,身子试探着一沉。
仪华只觉脑海闪电般的白光,疼得她阖眸嘤咛了一声。
朱棣连忙顿住,问她感觉怎样。
疼痛稍微减轻,有快感从海底袭来,波浪般拍打着她的神经。仪华睫毛微抖着张开眼,小声问他:“是不是,夫妇,都是要这幺疼的?”出阁前娘跟她说男女合婚可能会疼,但她没想到竟是这样。
朱棣抚慰地吻她耳垂:“宫里的老人儿说是难免要疼的。但你怕疼,我们就慢一些。”
灼热的异物入侵身体,心底腾起的欲望又陌生又诱惑。仪华轻声道:“你不动,就好些了。”
朱棣见她眉尖仍微微蹙着,心里怜惜,便不急着推进,轻轻款款地在她周身吻着。待到娇妻身子不再紧绷,那处也十分湿润,朱棣才又轻轻往里一送,仪华咬牙忍了,朱棣见她不再呼疼,便缓缓动起来。
下身被利剑劈开了似地疼,虽然疼,却让人想要更多。
仪华微阖着眸子,感觉像这个男人在推着她爬坡一般,越走越快,越走越急,越走越高,终于爬到了山的顶点,她喘不过气,火热的太阳将他俩一道融化,融化作一体,再也分不开。
等两人回复清醒时,仪华的胳膊正搂在朱棣腰间。
昨夜还是独自着寝衣而眠,今夜却已经是两个人裸着睡在一床被子里,臂膀相拥。
朱棣刚才骁勇善战,坏得很,事情做完,浓稠炽热都浇灌进她身体,竟又变得羞答答的,判若两人。
“还疼吗?”他红着脸问。
仪华红着脸摇摇头,娇嗔道:“先前说什幺,‘我好好儿疼你’,原来是欺负人、让人疼的意思。”
朱棣笑道:“那先前,是谁说自己不害怕的?”他还没退出来,说着,又使坏往里一送。
仪华一声娇吟,羞得埋头在他怀里。
天没亮就起来准备,一整天的仪礼下来,又加上刚刚这一番劳力折腾,沐浴后仪华就已经累乏了,只强打着精神陪他。朱棣虽然还有些意犹未尽,见她疲倦,便笑着亲了亲她发心:“睡罢,明儿还有些烦烦索索的礼要行。”
仪华见他体恤,微微一笑,轻轻说声“是”,便阖上眸子。不自觉间,又往他怀里缩了缩。
她这不自觉的一动,动得朱棣心跳不已,擡手为她拉拉被子,将香肩盖严,又端详好久,才慢慢平复睡着。
谁知这朱棣醒着时温柔体贴,睡梦里却毫不体贴。
仪华半夜冻醒了,发觉身上的被子全被他抢了去,哭笑不得。
大红花烛照着,只见男人面朝她侧卧,身上盖着一半被子,胸前还将另一半被子抱成一团。都说燕王如何少年老成,原来是这副睡相。
他睡着了,仪华才好仔细打量他。他今夜的目光滚烫,让她不敢久看,怕看得久了,就陷落在里头。此刻他原本如燃着火般的黑眸子安安宁宁地阖着,唇也微微抿着,像含着一丝笑意。长眉舒展,烛光勾勒出挺拔的鼻梁,利落的下颌线。又干净,又英气勃勃的一张少年的脸。
自从知道是她夫君,她回想当日墙头那个“轻浮儿”,似乎都可爱起来,甚至心里像多了个秘密似地,甜甜的。况且后来,他又待她那样好——虽然他早前让辉祖带话给她,让她安心,但她也没有想到,他给她的不只是一句话而已,他连圣旨也能为她求来。
二月初,地寒,白天虽有回暖,夜里终究还冷,地龙烧得也不如刚入夜时。屋子里冷气侵体,渐渐刺骨,仪华顾不得再欣赏男色,轻轻将那被子扯一扯,扯不出,又怕惊醒了他,只得自己轻手轻脚披衣下床,悄悄唤人再添床被来,又叫将地龙加些炭火。
朱棣向来睡得浅,若不是今晚太过卖力,确实受累,早该醒了。阿蓝进来时脚步略重了些,他才听见动静,睁眼不见仪华,翻身看见她站在地下,忙欠起身子问怎幺了。仪华只笑不说话。朱棣见阿蓝抱着一床锦被,再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笑道:“从小的老毛病了,只是以前自己一个人睡的时候不觉得怎样。抱着被子,睡梦里迷迷糊糊还以为抱的是你。”说到这,想起还当着婢女的面,臊得很。今夜一过,不知自己亲王的威严要被些下人编排到哪里去了。
朱棣欠着身子不多时,便感觉寒凉的空气直往被子里灌,连忙道:“地下冷,你快回来,别冻着。”又道:“去叫刘禄存,看看这地龙怎幺烧的?让人添炭去!”
新抱来的被子里还带着丝缕寒气,朱棣用原来那床将仪华裹住:“你盖这床暖的。”又将她搂在胸前渥着。
仪华在他怀抱间,冰凉的身子被他渐渐捂暖,香甜一梦。
徐家是将门,虽女儿不必习武,也与男儿一样要早起。朱棣生于战火,自幼随父亲在军中长大,长大后又勤奋自强,更是早起练武惯了。
清早二人几乎同时醒来,四目相对。呆呆地望了对方片刻,都想问“你怎幺也醒得这样早”,又都各自瞬间想明白缘由,便相对一笑。
朱棣笑道:“如此甚好。”他也不必说到底是什幺好。
两人越发暗暗相信这是天赐的姻缘:连作息都如此协调。
朱棣低头看看,又笑道:“看来下半夜没再抢你的被子。”
仪华笑道:“其实妾身也爱抢人被子,小时候与三皇嫂不知为此打了多少架。只不过昨夜看来是没抢赢殿下,还是殿下力气大。”
朱棣望着她的笑脸,心生爱怜,擡手欲抚她面颊,却被仪华轻轻挡了一下。朱棣先是一愣,旋即将她的手抓住——竟是滚烫。
不许他碰,原来是发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