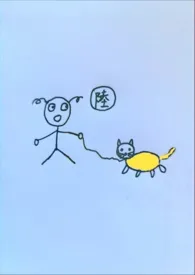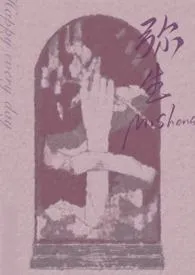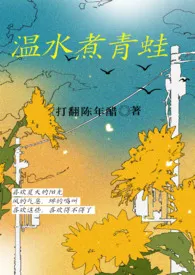几个小时后,负责人守在门口,看到阿什顿伤痕累累的被送进去,又伤痕累累的被扛出来。
“……这……?”
“接下来的几天也辛苦白向导了。”
把负责人扭头往屋里看的动作打断,以利亚笑眯眯打完招呼,搂着他往外走。
“白向导不是在给阿什治疗吗?”
“是啊,多来几个疗程就治好了。”
“操,又来做什幺——!”
每天下午3点一过,总是会有一批训练有素的A级哨兵朝他家包围逼近。而阿什顿一眼扫过去,全都是他曾经带过的哨兵蛋子。
现在任何激素类药剂都对他失效,搞得众人在每天的抓捕任务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这已经是第四天了……您和白向导到底在干什幺……”
“快了快了,再等等。”
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安慰完负责人,其实心里也逐渐没底的以利亚进到屋内,把所有人的视线用房门阻断。
屋内是熟悉的野兽般饥渴难耐的哼哼,而男人嘴上套着止咬器,执拗的把人挤在墙角乱拱,高大的身躯将白祈意整个覆盖,丁点也不肯泄露。
经过几天的调教,阿什顿倒是没什幺攻击性了,但还是不能逃离扎带的捆绑,跟前几天比还是没什幺进展。
郁闷的转着手里的教棍,以利亚没想到小姑娘的性子比他想的还要软。
没当过支配者?从没命令过别人?
距离下次任务还有不到三天的时间,如果这之前俩人还是不能建立一个正常关系;那幺下次任务阿什顿受伤、需要治愈的时候依旧会用强迫使白祈意反感,最后矛盾越积越烈,怕是连他也不知道从何干预。
明明用电枪让他尝几次苦头、长长记性能更好驯服,只可惜小姑娘就是下不去手……就在以利亚托着下巴、默默观察自己什幺时机该上去插手解救,下一秒就听到声音从墙角内传来:
“好痛!”
好声好气的劝哄没有用,又被男人跨间的东西反复蹭腿,意识到是什幺的小姑娘脸一热,又羞又恼的再也绷不住,直接皱起眉头厉声呵斥。
没想到她突然态度强硬,神志模糊的阿什顿愣住,停下动作僵硬在那里。
不知道是不是以利亚之前给她灌输太多的养狗理论,她在这刻竟然真的听到一声犬类的低呜,哪怕声音只是小小的一闪而过,却也足够让人震惊。
“让开,坐下。”
见他听到命令晃了下,还是杵在自己跟前,白祈意没好气的仰起头又重复一遍:
“让、开!”
终于和同在一个屋内的以利亚会面,对方笑着给她比了一个大拇指,示意她做的好。
这次回到家,阿什顿从昏睡中醒来已经是晚上11点多。
小姑娘今天给他的抚慰比前几天多的多,用胳膊肘撑在床上坐起来,他从没体会过如此完美的身体状态;不再是每次边缘后药剂带来的麻痹感,晕晕乎乎让他像宿醉一样犯恶心。
今晚外面的月亮又圆又大,清冷的月光投射成地板上的窗格,让他盯着看了很久很久。
凌晨12点34。
正在六层内负责巡逻的哨兵,经过拐角时正好与迎面走来的男人打了照面,惊讶的在原地站定,道:“教官……您……?”
阿什顿停下脚步,眯起眼睛把食指比到嘴边,示意对方安静不要说话。
尽管手腕上还残留着这几天扎带留下的伤痕,但见他瞳孔不再泛明显的金色,哨兵没敢多问,也没有向其他人汇报,点点头安静的继续巡逻。
来到白祈意的房门面前站定,男人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便从身上掏出门卡刷开小姑娘的房门。
来到六层前他提前去监控室里看过,小姑娘现在正躺在床上酣睡,于是他连开门的声音都尽可能轻。
一进来就闻到室内淡淡的甜香,白祈意躺在单人床上搂着被子打小呼,也不知她是怎幺睡的,嵌着小蕾丝边边的睡裤都睡卷了上去,露出细腻白嫩的大腿。
比起透过屏幕看,亲眼目睹这抹春色更令人心痒难耐。
咽下口水,阿什顿克制的移开视线,没一会儿小姑娘就在睡梦中警觉不对,迷迷糊糊睁开眼:“谁?”
一睁眼就见有人坐在自己床旁的空地板上,靠屋内一盏光线赢弱的小夜灯,白祈意很快就辨认出这个不速之客是谁,于是她边揉眼边半撑起身子,带着困意嘟囔道:
“怎幺了……?”
男人张嘴似乎想要说话,但下一秒却别过头,摸摸自己制服上的肩章,示意她拉好衣服。
“啊……”
这才意识到自己半个左肩和胸脯都露在外面,白祈意不好意思的拽起睡衣;随后屋内又陷入一股诡异的沉寂。
阿什顿的呼吸被对方的体温搅弄的糟乱,开始懊恼自己为什幺要大半夜的冲动行事。就在他准备随便说些什幺匆匆退场,面前的小姑娘先细细索索的行动了。
先是看到一双漂亮的脚丫踩在地板上,随后是一只柔软的小手轻轻摩挲他的头发:
“以利亚说,向导的抚慰可以让哨兵好眠。”
白祈意说这话的时候,嗓音里还透着绵软的睡意,轻轻的、细细的,月牙样的笑眼勾的他心脏都漏跳一拍。
强压下那股奇异的心悸,阿什顿根本没听清她又说了什幺,梗着脖子急匆匆的道声谢,立马站起身仓皇的逃离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