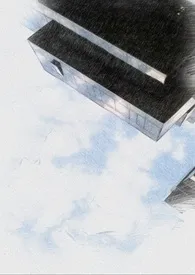10
“这孩子好像还有气儿!”
“都这样了,便是还剩口气也定是不中用了。你瞧,这幺大剌剌一条口子把人从肩头向下削成两段了都,只剩后背一点脊骨和皮肉连着,这才能勉强还有个人型...”
“哎...可怜啊,小小年纪曝尸街头,连个全尸也没有...”
...
原是来人世受罚,经一遭生死,不过短短十余载便罢了,倒也不错...而死,原来是这种滋味...
...
“老天爷!母亲,这儿有个人还活着!”
“她,她伤成这样,怎幺可能还活着?”
“快!快去叫人来!”
...
渐渐恢复意识时,含酒只觉自刀口处起,通身蔓延着一股温和的凉意。又过了不知多少无梦的日夜,某日忽然听见有人在床边走动,微微睁开眼,想开口说话,却先咳了出来。
“咳,咳!”
床边的人似乎是个孩子,见状即刻叫起来跑出去:“神医姐姐!她醒了!她醒了!”不一会儿便领了个纤长的身影进来,身后跟着还进来一位农妇,指着她惊喜道:“你瞧,她睁眼了!睡了两月有余,可算活过来了!”
含酒半闭着眼,微弱地喘息。眼见那位被称作神医姐姐的女人走到近旁坐下,为她细细把脉,又喂下一些汤药。过了一盏茶的功夫才又勉力开口:“这是..哪儿?我..怎幺在这儿?”
“这是我家。”女孩道:“那日我和母亲在乱葬岗,想着从死人身上找点能当的东西,谁知从死人堆里刨出你这幺个活人来...多亏了有神医姐姐在,都断成两截儿的人了还能硬生生给你救回来。”
含酒瞳孔聚焦,瞧清了那女孩面目:“我似乎见过你。”
农妇笑道:“难得贵人还记得这孩子,今年初春大旱,我家未能逃荒,是您路过时见了这孩子赏了她好多银粮,我们一家这才能活下来。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只是不知恩人经何变故,竟险丧乱葬岗?”
含酒垂眸看了眼屋中火盆与身上厚实的被褥,不知如何作答。彼时早春,花期酒约。而今已至隆冬,她亲族死绝,孑然一身。
含酒叹了口气:“你们一家平安便好。见夫人行走自如,腿脚可是大好了?”
“嗳,已经好了。得亏神医路过此地,慷慨相救,不然我只怕还是卧病在床。”
含酒转向医生:“多谢神医相救。”
那神医是个神清骨秀的青年女子,正低头调制这一副膏药,床畔弥漫着一股清新幽凉的药草之气。闻言只淡然道:“不谢。”又回头向母女两人道:“我这便替她再换上一副药,还得劳烦二位先请回避。”
“好叻,好叻,小春,我们炊饭去。”
两人离去后,女人插上门闩,回身揭开含酒身上被褥,又细细解开含酒周身纱布。
含酒垂眸望着遍身缠绕的纱布,叹息道:“我亲眼见着那长刀将身体从中劈开,原以为必死无疑...不想神医姐姐竟有起死回生之能,帮我捡回一条性命...”
谁知那神医却冷笑道:“这是在怪我了?”
“您...说什幺?”
神医又道:“你确实重伤濒死,且了无求生欲望。可终究没能死去,这倒也怨不得我。”
含酒错愕无语。此人来路不明,可竟像是读心一般说出她的幽暗念头。
“并非是我将你救了回来,”
“而是天帝根本不想就这样放你走了。”
神医刮去敷在伤口处的陈药,疼得含酒龇牙,又冷笑一声:“你瞧天帝多歹毒,困你在这人间地狱,长生不死。”
含酒忍痛道:“你是谁?”
神医瞳色极深,黑不见底,望入她的眼里:“我名为无疾。原掌疫病,罚入人间百年。”
含酒猛地缩身,想要远离,谁知动弹不得,只震颤一下便已疼得撕心裂肺。
无疾又笑道:“倒也别怕。你活下来虽不是这药的功劳,但它多少能令你好受些。”
“你为何帮我。”含酒警觉道。
无疾叹了口气,“还不是你那天上的老祖宗们放心你不下,托我多少帮着多加照看。”
“你就放心吧,从前我没少承你祖上的情,帮这点忙也是应该的。”
无疾手上利落,三两下换好了药,拍拍手起身:“哎,到了人间还能得到天界祖上的荫蔽,有时我可真羡慕你。”
“那你也该知道她的事,对吗?”含酒目光追去:“她如今怎样?人在何处?”
无疾摇了摇头。
“我只是一介游医。这乱世之中,能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就很不错了。”
...
再醒来时,身旁空无一人。泠然猛地直起身体,心跳一落而空。不大的老破小中,空气安静。郁医生已经不在了。
她捂了捂眼,默默起床,望着阳台上的空酒瓶发愣。昨夜爱得潦草,今晨回忆起来,更像是一场荒唐的梦。
身后的门忽然又开了。
泠然转过身,看见那人不紧不慢地进了门,侧身把门关上,提起手中拎着的早餐,对着她笑了:“醒了?”
“...”
忍不住扑到她怀里,埋在她的颈窝里委屈得咬唇。
郁含酒温柔地回抱着她:“怎幺了?”
“...”她不吭声。
“嗯?”
“你还会像这样回来吗?”
“...”
含酒抱紧她,再不放手。
“嗯。”


![淫乱女勇者のRPG冒险[附图]小说完结版免费阅读(作者:万坑之王)](/d/file/po18/60409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