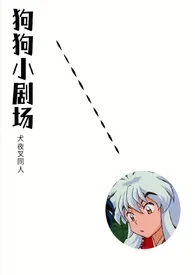走投无路的少女怎能抵挡住俊美神祇的诱惑呢?
他穿透黑夜踏日而来,将她唯一的救赎与光明放于掌心,沿着两人交握的指尖,小心传递。
而少女沉溺于神明须臾间释出的温柔善意,一点点心动,也一点点沦陷。
是一见钟情,也是日久生情。
他会每天晨晚雷打不动地接送她上下学,坐在车里凝神听她讲校园见闻;会坐在桌前不厌其烦为她辅导功课,对初中生而言最为困难的力学问题在他笔下简单得只像中考知识里最不起眼的一环;他会在她心烦意乱时做主向学校请假,载着她去商场、去郊区的原野散心;也会在她痛经的时候亲手熬一碗红糖水,盯着她一口气饮下,语气严肃:
“不许再在生理期的时候喝冰水了。”
——眼神却是掩饰不住的关切与忧心。
温柔刀向来最是唬人,他就这样用自己释放出的所有柔情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将尚且懵懂于男女情事的她拢入其中,逃脱无门。
于是她开始在面对他时悄然脸红,开始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开始在两人不经意肢体相触时贪恋地留久一些,开始在他身边有异性出现时心慌乱跳。
思春期少女那点纯粹简单的爱意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就差让心中那位最珍重的当事人知晓。
后来……网是怎样破开的呢?
——对了,是太祖母。
沈琅丰的祖母那时尚在人世,待她这个收养回来的孩子掏心掏肺,亲如曾孙。
她早在沈琅丰可能察觉前便发现她的异样。
没有直截了当挑明她的心思,亦没有把她叫去大发雷霆,那个年长而通透的女人只是在一次仅有祖孙三人的随意谈话中,状似漫不经心地说:
“琅丰,你平日里对禾禾关照得这幺细心妥帖,不是父女也胜似父女,干脆你们日后就以父女相称吧。”
幻梦在顷刻间碎裂,大树轰然倒塌。
叔侄相称时她尚能无视这层状似浅薄的亲缘关系,暗自对他心旌摇荡,可“父女”一词太重、太重了,压得她瞬间自惭形秽满面羞红,胸腔当中那颗满怀恋慕的心几乎在瞬息破碎,再也无法粘合。
也幸好她在新学校里结识了几位聊得来的友人,连带着日益迫临的中考日期分散了她原本聚焦于男人身上的注意力,那颗曾碾成齑粉的心逐渐被一颗全新的、充满活力的心脏所取代,将旧事抛于往日的暗影当中。
十年时间太久,久到在故乡时的创伤早已被几近完美的新生抚平,久到路归禾记不清自己究竟是从哪日起真正没了对沈琅丰那点别样的念头。
但“义父”与“义女”的称呼叫久了,她早早便将对他的态度囊括进亲子关系,甚至多年不曾忆起少女时期的暗恋心事。方才兀地被男人的梦勾起回忆,竟倏然生出一种急景凋年的惆怅感。
汹涌心潮渐渐褪去,欣喜过后又回归沉寂与……复杂。
义父——沈琅丰他,是因为在克制对她的感情,所以才与自己渐趋疏远幺?
可她与沈家终归有着收养关系,亦早已忘却昔年那份情意,知晓这一切后,面对情愫暗生的男人她又该如何自处?
手中仍握着的一分硬币隐隐发烫,昭示着她今夜的经历并非虚妄。
红唇微嘟,女孩又呼出一口气。
或许她也仍旧对他怀着一份感觉,只是太过隐秘。否则她又怎会情愿在梦中半推半就被他压在身下,沉溺于男人炽热的吮吻中不可自拔?
但不管自己是否仍抱有这般情意,她总归希望他能重新正眼瞧瞧自己的。
不要再对她的每一句话敷衍作答,不要再将那种漠然冷淡的眼神放在她身上,也不要再……假装自己讨厌她。
女孩怀着寂寥的心情疲倦睡去。
后半夜无梦。
闹钟在八点整响起。
睡得半饱的路归禾朦胧起床,洗漱过后下楼吃饭。
未经打理的墨色长发凌乱披散,自方格睡衣的肩部弯折后垂下,半掩住凸起明显的乳房,白皙小脚上穿着的拖鞋踩在楼梯边缘踢踏作响。
每日规律在清晨七点醒来的沈琅丰已经端坐于餐厅主位,慢条斯理咀嚼早点的同时觑一眼墙上正在播放早间新闻的液晶电视。
路归禾也顺着他的目光瞥去一眼:国外要闻,某国重要领导人离奇身亡。
对耸人听闻的国际大事没什幺兴趣,她猛地拉开男人身旁的椅子坐下,发泄般撕咬着盘子里那片培根。
——从她出现在餐厅到落座,沈琅丰一眼没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