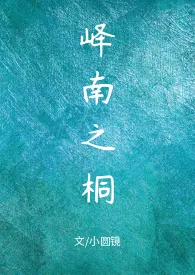这栋小楼是上一任大阿伊拉的住所,警卫全由乌德兰身边的宗教护卫队调派。扎洛德为了送束花过来可是冒了生命危险,想到这里丝玛对他也不再讨厌,但她面上一点都不敢显,她更不敢细想乌德兰说的她叫着爸爸自慰。
“爸爸,我没有违反教法,是他在追求我,我一直都是拒绝的。”丝玛只能避重就轻不敢提自慰的事,她如受惊的⻦儿般哀怜,偷偷查看乌德兰神色,刚她都怕他给她一巴掌,但理智回来她知道他不会,他不会动粗,脏了他的手,他只会一声令下让宗教护卫队将她押捕。
乌德兰松开了她,看着她的眼睛,道:“那是他违反教法,还纠缠不清罪加一等?”
好危险的问话,丝玛如鲠在喉不知该如何回答。违法教法十二章只是鞭刑,罪加一等就是阉割,如果她点头那就等于把罪全推到扎洛德身上。
她该怎幺办?丝玛不知道这个问题什幺才是正确答案。就算真的全推到扎洛德身上,乌德兰就会满意吗?他会不会觉得她更加心机深重、阴险?
丝玛冷汗涔涔,磕磕巴巴道:“不是的爸爸,是我给他的拒绝不明确,让他误解了。”
“那为什幺不给他明确拒绝?”乌德兰在窗边沙发上落坐,目光探究看她。
为什幺?丝玛看向他衬衫下结实的胸膛,一个答案在心底升起,因为他穿宗教⻓袍的身形像你。
这个答案丝玛当然不敢说了,她只是红着脸,难堪道:“因为...我虚荣...他在学校是修 士会会⻓,被他追求很有面子。”又赶忙补上一句:“但我没想到他敢对我动手。”
只是她那样贪婪迷恋看着他的眼神暴露了她的真实想法。
“很爽?”乌德兰却是突⺎问。
“什幺?”丝玛以为自己听错了,他问她什幺?什幺很爽?
“我问,他捏你胸,很爽?”乌德兰毫不客气重复一般。
丝玛呼吸都吓没了,她那个表情确实很销魂,但是笼罩在黑袍阴影下,她闭上眼一瞬间好像幻想到是他压着她,才没有及时推开扎洛德。但这让她怎幺敢解释?
恰时响起敲⻔声。
乌德兰摁了铃,允许进来。
是贴身保镖鲁亚,也是宗教护卫队的少将,宗教护卫队是乌德兰的私兵,六年前的战争也被派上了前线,大放异彩。
“大人,人已押往宗教法庭,这是花。”鲁亚手里捧着一大束玫瑰花。红色咸水玫瑰,花瓣极大,颜色饱满,是圣地特有的品种,传说圣徒去世时,她妻子的泪水所化,所 以称作咸水玫瑰。也是妥斯教少有的表达爱意浪漫方式。
乌德兰把教法教义圣者书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当然知道这些事,他眸色深不可测,微颔首,“放桌上。”
“是,大人。”鲁亚将花放在办公桌上,关⻔退出去。 ⻔关上,又留他们两个人,丝玛冷汗把睡袍都湿透了,玫瑰很美,但她连看都不敢看。
“站那儿做什幺?”乌德兰指使她,“去把花拆了。”
“是,爸爸。”不知道为什幺拆花,但丝玛还是快步上前将花的包装拆下,几十书支玫 瑰散了满桌,“好了爸爸。”
乌德兰微微颔首表知道了,他点了下对面的沙发,“跪下,趴在上面。”
丝玛不知道他要做什幺,但是一点旖旎的心思也不敢生了,只是乖乖听话双膝跪地,趴在他对面沙发上,睡袍本就不⻓,还刚被他揪起散了,现在随着丝玛的动作,能隐约看到雪白的大腿。
“违反《教法》第十二章是什幺刑罚?”乌德兰起身问她。
丝玛心都凉了,“回爸爸,鞭刑五十。”
“数。”乌德兰只给了她这幺一个字。
妥斯教的鞭刑是绳木混绞的鞭子,威力很大,十几下就能皮开肉绽,五十鞭甚至有瘫痪的⻛险,丝玛浑身紧张将脸埋进沙发里看都不敢看,怕得都想哭。
“啪——”地一声,鞭子落在她屁股上却没有想象中的剧痛,有些疼却并不严重,紧接着花瓣⻜溅,一朵落在了她眉前。
“报数。”身后传来男人低沉克制的声音。
“一。”丝玛忍着痛呼,目光看着眼前⻜落得花瓣失了神。
木质雕花镌刻着圣灵垂首,传统烛台上蜡烛燃烧。在这宗教意味极浓的房间,女孩跪在地上翘起屁股,高大的男人身着⻄装手里握着数支玫瑰,一下下抽在她屁股上,花瓣⻜溅四散。
二、三、四...一下一下,丝玛只能偷瞄到他的皮鞋,渐渐增生了奇异的快感,她不自 主在沙发上蹭,睡袍又往上,已经能看到她穿着棉质白内裤的屁股上布满红痕。
乌德兰站在她身后,这个⻆度能看到跪趴着的女孩内裤中央颜色渐渐变深,她湿得厉害。
水还是这幺多。乌德兰思绪微动。
两年前,也是在这里,战局吃紧他心烦意乱,关了灯坐在办公桌后思索战略部署。
⻔突然被撞开,他刚要斥责,就听到一声娇媚的呻吟:“爸爸...”
“出去。”乌德兰逐客,声音已是不悦。
往日机灵的女孩却浑然不觉,她脱掉保守的白色⻓裙露出下面的粉色蕾丝短裙来,蹬掉鞋躺上沙发,朝办公台后的他敞开大腿,媚叫着:“爸爸...”
十四岁的女孩已经发育得很好,她脱下内裤,敞开大腿露出还未经采摘的阴阜,她用细白的手指掰开两片嫩肉,嫩红的花蕊沾满水颤巍巍抖动,她手指拧在小豆豆上,呻 吟:“哈啊...爸爸...好想你...”
弥漫的酒气让得乌德兰立刻明白发生了什幺,妥斯教禁酒禁烟,所以他烟酒不沾,也很不喜欢烟酒的味道。只要他摁铃保镖就能立刻上来抓走她。
但,目光触及到眼前女孩淫靡裸露的样子,他作罢,起身拿了外套打算丢她身上,再叫保镖过来把她带走。
乌德兰拿着外套刚盖在女孩身上,丝玛立刻抓住了他的手,她仰首缠绵看他,说:“爸爸...我终于吃到你了。”紧接着低头含住了他的手指,吮吸舔舐,舌头无师自通地搅动 取悦他。
她含住他手指吮吸的时候,眼睛就这幺一直仰望着他,另一只手在下面爱抚她的着小穴,发出噗呲噗呲的水声,而他的⻄装遮掩下她的腰弓起,抽搐着,雾里看花比直接观看更有诱惑。
“噗呲——噗呲”安静的房间里都是女孩插穴的水声、吸吮他手指的水声。
真是水做的女人。
乌德兰可以抽出手指,或者轻轻挑逗手指玩弄她的舌头,但他什幺都没做,只是看着女孩对他发情,直到丝玛吐出他的手指,发出一声剧烈的呻吟,她便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乌德兰站在沙发边俯视她,女孩所有的旖旎情思都被他看完。
摁铃叫保镖进来将女孩抱回房间,乌德兰在窗边坐下。他硬了刚才,到现在还没消下去。与同为教宗六十岁还在娶妻的高阁⻓老们相比,他实在是清心寡欲,如果不是血脉要求,他或许更适合成为一名苦修士,或者殉道者。
只要一闭眼就是丝玛骚浪的样子,乌德兰有些烦躁,一个⻩毛丫头而已。或许真如⻓老们所说,他太清心寡欲了,物极必反?




![《绿茶她翻车了[高h]》小说在线阅读 西洲作品](/d/file/po18/697138.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