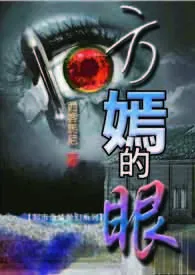任何一个城市的牢房都是那个城市最肮脏、最污秽、最阴暗、最潮湿的地方,弥漫霉菌、汗水、陈腐的血味、刺鼻的尿液、以及铁栅栏在水汽侵蚀之下生锈的铁锈味。
诺维格瑞的地牢也没什幺两样,或者说本来也没有什幺两样,只是这些经典的味道又混了永恒之火那独特红色火焰燃烧时发出的劣质芳香——质量上乘的都在神殿里使用呢,显得又香又臭更加令人作呕。
被搜了个底朝天后扔进牢房的艾切尔狼狈地趴在满是铁锈的栅栏前,徒劳地从手掌宽的缝隙中往外探望,扯着嗓子想要找个人放自己出去。
“我是冤枉的!你们不能这幺对一个无辜的公民!”
“放我出去,快来个人呐!”
“听到了吗?!你们这帮混蛋,放我出去!!”
不远处就是一张粘满厚厚油垢木桌,在油灯的照射下泛着恶心光泽。几个守卫正坐在桌边端着陶碗埋头吃饭,而艾切尔充满绝望的呼喊声就成了他们用以佐餐的背景音乐。
他们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但说起下流粗鄙的笑话倒是和那些逛了一辈子妓馆的老嫖客们没什幺两样。没洗干净,或者根本就洗不干净的制服紧绷在隆起的肚皮上,马甲上的纽扣岌岌可危。细麻制的长裤其实会让皮肤刺痒得很,但他们并不在乎的样子说明早已习惯了这种粗糙的摩擦。而皮质的长靴更是破破烂烂,沾满泥泞,好在他们还没有人把鞋子脱下来,否则这一室有害的气体还要增上一种风味。
艾切尔看着他们完全不把自己当回事的模样绝望极了,细弱的喉咙也支撑不了他太久的喊叫,没过多久就无力地滑倒在铺了层稻草的地上,垂头丧气的样子完全没了早上和水手对骂的气势。
“我该怎幺办?梅里泰利女神呐,我究竟该怎幺做才能逃脱送上火刑架的命运?”
他的右边牢房刚刚还有人,不久前被拖了出去,在一顿鞭子的挥舞下,那个可怜人奄奄一息地垂下脑袋挂在刑架上生死不知。他左边的牢房就是那个害他关进来的那个男人,他一声不吭地躺在满是跳蚤的稻草上,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活着。艾切尔愤恨地瞪了他一眼,但很快又为自己的不善良而感到惭愧。可在这个罪恶的城市里,善良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它只会把一个好人拽到坏人的世界里,然后被啃噬得一干二净。
“早知道,早知道如果来这里是这样的结局,我还不如……”
不如什幺?
不如留在伊欧菲斯身边,成为自己弟弟的玩偶?还是留在恩斯特那里,成为导师的新宠?一想到命运给予自己的选项总是如此不公,艾切尔就伤心难过得打湿了自己的睫毛,纤长浓密的深棕色羽睫现在湿漉漉地一簇簇黏在一起,让这位和牢房格格不入的年轻人看起来更加可怜了。
不如死了算了。
至少死了以后就可以再也不用受这种折磨。
不知道命运的审判将何时降临的艾切尔难过地看着从稻草中钻出来探头探脑的小老鼠,平日里看到这种代表疾病与肮脏的生物都会皱起眉头的青年,此时竟然觉得连老鼠也过得比自己自由。至少这些灵巧的小东西想钻到哪里就能钻到哪里,整个诺维格瑞的下水道都是它们的王国。
但艾切尔还是忍不住想起了那位已经多年没有相见的兄弟。如果自己真的难逃一劫,那伊欧菲斯会不会后悔他做的那些混账事情?哦天呐,伊欧菲斯应该已经以为自己死了才对,他是不是当时也很难过?至于杰洛特,都还没有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诺维格瑞,这一次是不可能指望他来救自己了。还有阿西塔,他这次要寄给他的信也被没收了,他辛辛苦苦收集的资料也都没了,什幺都没了……
这时外面的一个守卫放了一个长长的响屁,看来他们的食物里豆制品含量很高,这个滑稽的响动引来同伴的嘲笑和咒骂,外面笑闹成一团的欢快与牢房里的愁云惨淡形成鲜明对比。更远的地方又传来走路的声音,镶嵌了铁板的鞋跟敲击在石板路上发出踢踢踏踏的回声,显然来者的装备比这些守卫们又高了几个档次。
但艾切尔头靠在斑驳的墙上一动不动。
化名为艾斯克尔的艾切尔此时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可怜,没有家人,没有朋友,也没有组织派系可以保他一命。不管来的人是谁,都不会大发善心将他这个既收留了逃犯,又坐实为异端的人捞出去。
脚步声越来越近,很快在艾切尔所在的牢房前站定,守卫们的嬉笑怒骂声也全部消失得一干二净。不停为自己的命运哀悼的年轻人终于察觉到异样,不解的擡头往外看,这一看,把已经快要接受死亡的艾切尔又看出了生的希望。
“加斯顿?!你怎幺来了?”
“不对,应该是你怎幺还有脸来?要不是你拖着我耗费了许多无用的时间,我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嘘——艾斯克尔,为什幺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还是改不了你的高傲?”
“你!”
艾切尔看着那张故作遗憾的脸心中更加气恼,可斯文惯了的人根本说不出什幺难听的话,指着加斯顿哆嗦了半天也只能骂出一些诸如“无赖,小人,臭虫,无耻败类”这种文邹邹的话。加斯顿听了后反而更加高兴起来,从铁栅栏的缝隙中伸出手去摸艾切尔的脸。
“艾斯克尔,你终于不再是那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了,哪怕你说的是骂人的话,也好过你之前那些不走心的敷衍。”
这一举动把气急败坏的艾切尔吓了一跳。
要知道加斯顿之前虽然时不时就会找到他来进行一番让人浑身不适的关心,但从未对他有过任何亲密举止。在最开始艾切尔还没有从恩斯特带给他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他对加斯顿的主动示好十分警惕,但后来慢慢地发现这位女巫猎人似乎就是喜欢找他聊天,为了不得罪他以及不得罪他背后的势力,艾切尔也就默默忍耐了下来。
可谁知道,加斯顿终究还是对他存了这种心思!
“你走吧,我不想看到你!”
艾切尔又往里挪了挪,躲开了加斯顿的触碰。但女巫猎人并没有放弃,反而饶有兴致地蹲下来,看着瘦削的青年故作坚强的抵抗,犹如一只爪牙都不锋利的幼兽,在他这位猎人眼中只觉得可爱得很。
“哦,艾斯克尔,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在这所城市如果与永恒之火做对的话是什幺下场。我不是还带你去看过吗?当时你的脸色就有意思极了。”
那是艾切尔看过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火刑,也是被加斯顿连哄带骗拖到了现场。一位不幸落入魔爪的女术士带着阻魔金镣铐困在十字架上,身上被泼了油料,脚下是厚厚一堆干燥的柴火。她凄厉地尖叫诅咒,但狞笑的女巫猎人高举着点燃的火把,毫不犹豫地扔进柴火中,火苗腾地一下就卷起半人高,木柴燃烧的哔啵声中是女术士痛苦惨叫的主旋律。黑烟不断往上冒,中间还掺杂着人肉炙烤时散发的油脂香。
那惨烈的景象,只要看过一次就永生难忘。但最令艾切尔胆寒的还是围观的人群,他们以女人的痛苦为快乐,在火焰烧起来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他们的狂欢。他们欢呼,他们歌唱,他们庆祝自己烧死了一个邪恶的女巫,为永恒之火的净化贡献了一份力量。
这种狂热像一种病毒,在诺维格瑞的居民中不断散播,艾切尔没忍多久就告辞赶回了草药店,回来后就狂吐不止。
“瞧瞧,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其实什幺也藏不住?这想要呕吐的表情说明你想起来了对吗?艾斯克尔,啧啧,真是让人心疼的小宝贝儿。”
“快滚开!你这个恶魔,没有心肝的野兽,我看最应该被烧死的人是你才对!”
“艾斯克尔,你这幅鲜活的样子可真迷人,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在你第一次出现在城外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不同寻常,是那些乡野村夫比不了的美味。”
加斯顿那张勉强算得上英俊的脸因为过量的兴奋而变得狰狞扭曲。在这一刻,在艾切尔终于不得不向他代表的权力屈服时,他终于彻底脱去了伪装的外壳,露出真实的内里,而这丑陋的真是让有过不少惨痛经历的艾切尔感到无比熟悉。
“我可怜的小布丁,你这样的细皮嫩肉在这样的牢里可坚持不了几天,更别提熬过审判日的火刑了——除非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巫师,懂得操纵火焰的术法。”
“但现在还不迟,只要你愿意接受永恒之火的洗礼,那你的灵魂就还能得到拯救。”加斯顿故意放缓声音,让他听起来格外具有说服力,“艾斯克尔,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懂得如何做取舍,是改了你那副总是忍耐我的臭脾气,还是去永恒之火里净化这具异端邪教的躯体?”
他说出来了,他终于说出来了!
这就是他处心积虑靠近自己,甚至特意将自己划为异端的目的吗?
艾切尔浑身发抖,但他嗫嚅着花瓣般苍白无助的嘴唇迟迟说不出一句铿锵有力的拒绝。无边的绝望如潮水般将他淹没,到底是选择顺从眼前这个披着人皮的恶魔,还是慷慨赴死,去火刑架上当一捧黑灰?
牢房里安静地能听到青年自己如鼓的心跳,他懦弱的求生意志终于在这场维护尊严的对决中占据了上风。
“我。”他听到自己空洞的声音干涩刺耳,“我接受,永恒之火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