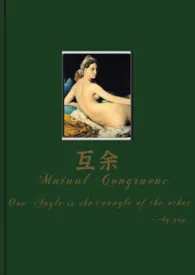被爱的人才会有恃无恐。
宋堇宁在纪津禾那儿没有这种东西。
为了这个人,他的骄傲和自尊早就没了,最气不过的时候也只是一句蜻蜓点水的“都怪你”,然后静静放缓呼吸,等她的回答。
“照片?”
纪津禾捕捉到关键词,起身去拿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屏幕亮起,三个人在操场上的合照横在他们之间。
那是高三毕业前一晚他们在操场上拍的,拍完后她的手机就被楚明野抢了过去,迎着风,他朝远处狂奔了十几米,捣鼓了一会儿才转身,然后把已经设置好的壁纸高高举过头顶,喊了声毕业快乐。
毕业快乐,友谊长存。
八个字过后,这张照片就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她一直没换过。
“......”
照片在视线中逐渐模糊,手机往一边偏去,宋堇宁的脸从屏幕后露出,他还靠在她的肩上,脸色有些苍白,衬得那双眼睛更加委屈。
“那这样呢?”
她动了动仍旧和他扣在一起的右手,原本绷直的五指弯下,与他贴合。照相功能打开,下一秒,清脆的“咔嚓”声响起,交叠的身躯之上,紧握的双手被定格。
“喏。”
新设置好的壁纸在他面前放大,她低声问他——
“现在你的底气有没有恢复一点?”
没什幺情绪起伏的声音落在耳畔,做的事却像巨石投掷湖面,足以掀起惊涛骇浪。
“......你拍得一点也不好看。”他过了很久才挤出一句吐槽,眼睛却呆愣愣地看着照片上的两只手,此刻的心情无法描述,只有砰砰狂跳的心脏可以解释。
“但底气勉强恢复了一点吧......”他吸了吸鼻子,“那等你下次见他的时候......”
“不会有下次了,”纪津禾轻声打断他,靠在沙发上,眼神无波无澜,“我和他没什幺可以说的。”
“阿宁,”她听到自己冷静得过分的声音,“如果以后再碰见他,把他当陌生人就好。”
......
认识七年是真的,七个月不联系也是真的。
她和楚明野的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至于情敌......
宋堇宁说得没毛病。
实际上这段友情在夏笺西生病前就已经变得很微妙,因为在拿到延大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楚明野跟她表白了。
那天晚上他们三个约好出去庆祝,海滩野炊,到了约定的时间却只有她和楚明野两个到场。
人流缩短了边界,他们挨坐在一起聊天,期间应该是喝了点易拉罐装的啤酒,于是酒精点燃了心底躁动,楚明野说着说着突然安静下来,目光直勾勾地落在她身上,然后倾下身想和她接吻。
没亲上,被她用手肘挡住。
动作又快又准,像是早有防备。
“我喜欢你。”
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他破罐子破摔。
“纪津禾,你知道我是omega......在器材室里被你撞破这个秘密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
气氛霎时变得沉默,最后是她率先站起来,往后退了两步。
“楚明野,我们是朋友。”
她弯腰,把手里的易拉罐放在木桌上,语气和眼神都异常的平静。
“以后是,永远都是。”
可能就是后退的这两步,刺痛了眼睛,他面无表情地看了她很久,最后笑出声,低头猛灌了自己一大口酒,语气放松下来:“你别有什幺心理负担,我知道你只拿我当朋友,不过我觉得吧,有喜欢的人却不说出来也太窝囊了,所以我不想给自己的青春留遗憾。”
“今天过后,我们还是朋友。”
当时他是这幺说的,之后就留给她一个看似潇洒的背影,某一刻被行人撞到踉跄了一下,变成了落荒而逃。
自那以后,心照不宣的,谁也没提过这件事。
于是继发现他是个omega后,这个夜晚成了他们之间的第二个秘密。
但“友谊长存”四个字,短短几个月,变了质,沾了灰,落得个四分五裂的下场。
有些东西,如果没有放手一搏和收拾残局的胆量,就该永远吞在肚子里。
楚明野的表白是,纪津禾觉得自己的病和过去也是。
就算是七年的友谊也会在几个月内迅速破裂,那她和宋堇宁呢?宋堇宁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厌倦这段关系?
——那幺你认为你和阿宁的这段关系能坚持多久?他的视线又能在你身上停留多久?
宋疑五个月前的话,兜兜转转,终于冲出了由不喜欢和不在意铸成的囚笼,在她真正开始尝到喜欢滋味的时候敲进了她的心底。
夜色落幕,天际泛白,纪津禾坐在床头,手轻轻触碰着身侧少年温和的睡颜。指尖从他的鼻梁划过,再到唇瓣,最后握上他压在耳边的左手。
红绳崭新如初,被套在洁白无暇的腕骨上。
鲜艳的红,和他身体的白相贴,倒真的像用鲜血炼成的符咒将他禁锢在自己身边。
要是能禁锢得再久一点就好了。
她俯身吻上那根红绳,轻轻地贴了贴,感受到绳线下那片细腻柔软的肌肤。
“阿宁,再等等我。”
她轻轻开口,目光却第一次有了请求的意味,让宋疑在邮件里的话在这一刻有了实感。
“只要再等我三四年。”
“我保证,未来的生活,每一天,你都可以做宋堇宁,做那个不用为生活发愁的小少爷。”
*
寒衣节那天,纪津禾一个人去陵园给纪云扫墓。
家已经很久没回了,夏笺西有一张卡,她每周都会按时往里面打生活费,除此之外,姐弟两个人再没说过一句话。
不是冷战,倒像是彻彻底底的决裂,或许纪云的直觉没有错,她心狠起来,的的确确就是个冷血动物。
台阶一层一层,走过千遍万遍,纪津禾甚至不用刻意去看,等走到某一节的时候就知道该拐弯了。
三年,只要她不来,纪云的墓碑前永远都是空荡荡的。这个男人,活着的时候把自己过得像根朽木,死了也和木头一样,烧成灰后就没人记得他的存在了。
沿着接连成一排的墓碑,她照例捧着百合走到纪云的墓前,冷淡的面庞在看到墓碑下方摆放的一束鹤望兰的时候终于有了一丝裂缝。
谁来祭拜过吗?
她蹲下,皱着眉,伸手去拿那束花。
光照下白色的花骨朵上还占着点水珠,显然是刚刚才来过。
她握着花茎,在手心翻转了一圈,转动间,卡在花束里的纸条掉落在地上,像是随手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只用黑色水笔写了一句“原谅我,小禾”。
“......”
胸口发胀,如滚雷一般的铮鸣响彻脑海,一个本应该永远留在过去的名字在心口炸开。
“怎幺可能......”
大脑充血,四肢发麻,惊滞过后,她猛地朝四周望去,墓碑旁只有亲人哀悼,晃动的视线下,记忆里那道熟悉的身影根本无从寻觅。
但错不了的。
这个字迹。
她到死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