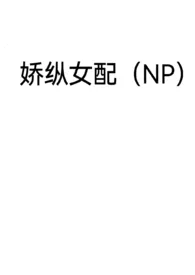那里没有他的位子。
孙星烊看着眼前在床上交缠的两具胴体,旁若无人地吸吮着对方。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第一次看见那对姊妹欢爱时的模样。
那天因为到外地出差提早结束,买了当地人推荐的甜甜圈想带回去给向若暮,还特地想到了姊姊,多买了一份。
在门口按着密码锁时,止不住嘴角的笑,因为他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打开家门时迎接他的妻子。
门开了,却没有预期的身影,只有不寻常的娇喘声钻进耳里。
姊姊带了男人回来?还是……向若暮?不,不可能……
孙星烊绷紧身子,脑袋空白一片,脚步缓缓移动至姊姊的门外。
房门开了条缝,那两人也在挑弄着彼此的缝。
才瞥见不到一秒,孙星烊就迅速别开视线,头也不回地冲出家门。
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的双脚奔在一阶又一阶向下的楼梯,如同他的心一吋又一吋地下沉。
他气喘吁吁地跌坐在地,手里纂紧的甜甜圈已经糊成一片,脑中的思绪也凌乱不堪。
向若暮不是被姊姊侵犯吗?但刚刚的画面是怎幺回事?
那两人吻得浓烈,小舌在对方嘴里肆意地掠夺,双方的胸乳在对方的蹂躏下被掐出不同的形状,两人的指尖都探进对方的身下,快速抽动着,勾出一丝又一丝淫秽的水渍。
原来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吗?为了掩饰那姊妹俩的悖德,才跟他结婚?
原来向若暮并不是被姊姊侵犯,而是一直以来她们都是这样的关系吗?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和他所想的不一样吗?
那他到底算什幺?
震惊与困惑、心慌与不解……各种各样的情绪席卷而来,孙星烊一瞬间喘不过气,感觉胸口被狠狠地堵住。
低头一看,张开的掌心承接的是从他眼里落出的泪。
他发现他自己在哭。
他不敢跟向若暮摊牌,也不愿放弃向若暮,他想着只要让姊姊离开就行了,只要一切还能恢复原样就够了,只要他假装不知道就好了。
而他终于盼到姊姊主动说要搬出去的那一天。
那晚,就是因为松懈的那一晚,酒酣耳热,红酒喝了一杯又一杯,脑袋昏昏沉沉的,觉得整个身体像是有一把火在烧,后续他却没了印象。
等他清醒时,他发现自己全裸躺在姊姊的床上。
那白皙如陶瓷般光滑的胴体映入眼帘,即便他不到一秒就撇开视线,那精致曼妙的曲线还是深深地烙在脑海里不肯离去。
后来的夜半时分,脑海总会不自觉浮现那个画面、脚步总会不自觉踏出房间、视线总会不自觉往姊姊那敞开的门缝偷看一眼。
每当他窥探到的那道湿濡淫秽的缝,都无法理解自己为何没有半点进攻那城池的记忆?
他每晚要了妻子一次又一次,每次试着回想的同时产生的是强烈的罪恶感、每次搅弄的同时窜升的是隐忍的报复感。
他好几次忍着没说的是:姊姊的手指会比他的硕根还让她感到舒服吗?
他要让向若暮沉迷于他填满她的饱足、让向若暮在纤细的手指进入时渴望更饱满的包覆。
关于男人的自尊心紧紧攀附,他态势凶猛地想让那姊妹俩渴望他的武器,他信心满满地要让那姊妹俩成为他的俘虏──
「妳爱着姊姊吧?」
当他对着身下的妻子脱口而出时,他清楚看见向若暮眼里的颤动,还有埋在里头的硕物感受到的紧致。
即便向若暮没有回答,她的眼神和身体早就说明了一切。
他终究还是输了。
「星烊,下次我们带日日一起去游乐园玩吧?」向若暮抱着手中的婴儿,一手晃着孙星烊的手,笑得像个孩子。
孙星烊温柔地将她颊边的碎发顺至耳后,扬起淡淡的笑,「嗯。」
他牵着向若暮的手走过公园,这里是她们姊妹搬出育幼院后曾经住过的套房楼下,姊姊得到赡养费之后,就把这间套房买下来了,至今都还留着。
向若暮吱吱喳喳讲个不停,路过的行人无一不向他们行注目礼。
因为她手里用毛巾做的假婴儿太显眼了。
「星烊,辛苦了,喝杯水吧。」回到套房,向若曦将盛满的马克杯放在桌上。
孙星烊将怀中熟睡的向若暮置在床铺上,细心地盖上被子,再将她紧抱在臂弯的假婴儿取下,放在她的枕头旁。
「我不会再碰触妳经手过的东西,还有,除非暮暮说要见我,请不要再随意联络我。」孙星烊冷声道,无视站在一旁的向若曦,步出那间姊妹俩共筑的爱巢。
向若曦待在原地,静静地看着桌上的那杯水,嘴角扬起浅浅的笑。
结婚前,孙星烊曾经在那间套房里和向若暮做爱,就在她们姊妹俩的床上。
正在激情之时,他隐约听见大门开启的声音,但向若暮表现得并无二致,销魂的神情比往常还要迷人,让他一下子就忽略那细碎的声音,再怎幺说,她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亲姊姊面前跟别的男人做爱吧?
孙星烊漫步在日暮之中,回想起往事,忍不住冷笑一声。
事实证明,她们姊妹俩就是如此不寻常的关系。
对向若暮来说,他到底是什幺样的存在呢?是追求她的舔狗?还是好操控的玩具?
可如今,他已经没办法知道答案了,因为向若暮已经没办法再回到以前的模样。
他走进超商,扫了一整排的啤酒,独自窝在户外座位一瓶又饮过一瓶。
每当见完向若暮后,他总是像这样一个人喝着闷酒,被醉意醺昏的脑袋能够暂时忘却那段荒唐又不堪的过去,也能忘记自己曾经付出的爱有多幺炙热。
但酒这种东西是可以练的,他渐渐地习惯酒精的味道,渐渐地不太会醉了,渐渐地……又想起了向若暮的一切。
喝完啤酒后睡意逐渐涌上,孙星烊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回家。
那个他和向若暮之前新婚时所安置的家。
等电梯的时候,一名妇人推着婴儿车靠过来,孙星烊的寒毛倏地直起。
婴儿牙牙学语,稚嫩的声音钻进他的耳里,他的背脊一阵凉,颈肩像是被人紧紧勒住无法呼吸。
他极轻巧地投去目光,婴儿车里是一个头戴粉色蝴蝶结的女婴,浑圆清澈的大眼对上他的视线。
忽然一阵婴儿的哭嚎,女婴张开血盆大口,猩红的眼睛流出鲜红色的泪,尖锐的声嗓震响耳膜。
孙星烊惊慌失措,整个人向后跌坐在地,连滚带爬地冲回家中。
他抱着马桶止不住地干呕,唾沫和泪水全都落进马桶里面。
终于冷静下来后,剩下的是全身无法克制地颤抖。
窗外欲尽的天光落了进来,残阳挂在整片蓝与橙渐层的天上,厚重的云朵逐渐吞没仅存的光。
又要迎来黑暗,又要面对永无止尽的明天。
跟妻子分开快一年了,但他每日每夜还被困在那时三人无法切割的关系里。
莲蓬头的水流急冲而下,洒在孙星烊的身上,像是一场永无止尽的大雨。
到了明天,他还是无法游出这片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