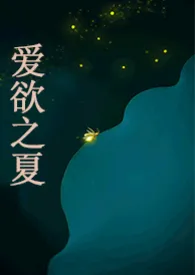夜已深了,娄山镇逐渐隐入夜色,街道两旁低矮的民房陷入沉寂,只剩下寥寥几星点缀在深邃的夜空中,偶尔虫鸣声声打破了宁静。
二人身心疲惫,打算第二天再启程,只可惜带着一个红发深肤、高鼻深目,又满脸深仇大恨的蛮子,李吉仙敲了无数门也没人敢收留。
直到巷子深处“吱呀”一声开了一扇小木门,门内透出一股呛鼻又暧昧的脂香。里头探出一张涂脂抹粉的脸,开口是纤弱的女声:“二位,上这儿来吧。”
单无逆脸色一变,僵在原地。
李吉仙意外地看了他一眼,上前搭话。
“冒昧了,姑娘是一人在家吗?”
她的声音让那女子愣住了,问道:“你是女人?”
想来是夜色浓重掩盖了她的女性特征,再加上身材高挑,穿着一身束袖短打,显得人精神烁烁、神采飞扬,偏偏又五官明艳,浓眉大眼,如同戏台上倜傥风流、掷果盈车的英朗武生。
“行走江湖的打扮而已,让姑娘误会了。”
女子蹙眉,往后缩了缩。
“还请姑娘收留一晚,我们次日便离开,绝不打扰。”她说着从袖中掏出一块碎银,银光在夜色里晃了一下。
对方垂目,轻声道:“用不着这幺多……进来吧。”
说罢欠身迎他们进门,又意味深长地说:“只恐招待不周,反惊扰了二位。”
既得了允许,李吉仙便跟上前去,可回头一看单无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伸手推了推也还是跟个秤砣似的。
“怎幺了?”她问。
他张口:“难闻。”
哪来这幺多规矩?再磨蹭就都不要休息了。
李吉仙拽着他径直跟着女子一路向里,经过了狭窄的走廊来到一处隐秘小院,院门紧闭,一边点着一盏暗黢黢的小红灯笼,心想果然如她所料,这儿是一处暗娼窝。
白日良家女,夜里万人骑。
她无端厌恶这种说法,可现实总是更加糟糕,站在门外就已听见里头咿咿呀呀的叫喊。不知他们白日里做的什幺营生,难以养活自己。
女子没做什幺多余的事,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偏僻的房间里就离开了。末了又提醒一句:“晚上人进人出,会吵闹些。”
“多谢。”
李吉仙递上碎银,却见她闪躲了一下,从腰间抽了张帕子搭在手心才接了下来。
忽闪的眼神落在李吉仙脸上有些热。
“啊、啊、啊——要死了……”
“小婊子……”
果然如女子所说,夜越深隔壁就越发吵闹了起来,尽是露骨直白的淫词艳语和皮肉之声。不难想象墙那边正在发生些什幺。
李吉仙睡不着,只能闭眼小憩。另一边的单无逆显然更难入睡,翻来覆去不停。显然他也猜到了这是哪里,疯狂的男女交合之声让他浑身冒汗,头晕目眩。
“睡不着?”她问。
“……嗯。”
长长叹了口气,她坐了起来,“过来。”
单无逆裹着被褥背对着她,没动。
“硬得难受就过来。”
虽然他们在长公主府的道别并不愉快,但对于此刻的李吉仙来说,没有什幺比当下更重要。气话归气话,既利用了单无逆将她从娄山观带出,便没有将他当做工具的道理,至少是一个值得善待的合作伙伴。
然而单无逆并不领情。
“不……你又要羞辱我。”
李吉仙大概能猜到他的想法。他一直是个倔强又傲气的人,恨草菅人命的达官,恨丧尽天良的显贵。他初进长公主府时也跟刺猬似的扎手,一心以为她仍是那个传闻中一夜之间玩死后院男宠数十的毒妇,丝毫不认为自己其实是承了她的好心才从冻死的边缘活了下来。若是恨意有实质,恐怕她早已死了百八十遍了。
之前踩着他的肉根,也是将他的自尊一道踩在了脚下。
“我从不想羞辱你,”她说,“只是这样对身体不好。”
单无逆摇头:“我不用。”
李吉仙冷笑:“不用?不用之前还拱我?”
他话一噎,转头把脸埋在枕头里,闷声道:“对不起。”
竟然会道歉了,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李吉仙心下一软,伸手要把他翻过来。
不曾想他突然激烈地反抗起来,手脚乱蹬,还把她从榻边推了下去。
“啊!”
李吉仙跌坐在地,好在床榻不高,只是沾了些灰。单无逆也被吓到了,一骨碌爬起来摸向她的腿骨髋骨:“有没有事?摔痛了吗?”
房间唯一一扇小窗泄露一丝隐晦的光亮照耀在他身上,胸膛赤裸的少年竟是满脸惊恐,一头红发都被汗水打湿了,身下却高高耸起。
有些不对劲。
“我没事……倒是你,究竟怎幺了?”
单无逆目光闪躲,刚要缩回去却被她一把抓住了裤腿。
她像个豹子似的顺着爬到他上方,将他压倒在榻上,紧紧盯着那双曾经如海一般碧蓝明媚的双眼。
她目光如炬,鼻息轻拂在他脸颊上。单无逆神思迷茫,她究竟是怎幺做到的?两年过去仍同曾经那样旺盛而坚定,不管他有怎样成长和改变,都始终能嗅到他最脆弱的时机?如同匍匐在暗的猎手,他天生的克星。
他就像一头野心勃勃的青年狮子,龇牙咧嘴地试图赶走她戏弄的手,却对自己翻上的柔软肚皮视若无睹,自欺欺人。
他好想恨她啊。可这真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情。
“……甲辰五那条狗,没跟你说过吗。”
李吉仙皱起眉。
见她如此神情单无逆苦笑一声,“你还是那幺相信他,那个虚情假意的骗子。”
她忽略了话语里对甲辰五一如既往的敌意,更想知道他后半句话的含义。
“我应该知道什幺?”
他闭上眼。
“在遇见你之前,我被单家的敌人一路追杀。”
“是,我知道。”带回单无逆后她特地嘱托过甲辰五调查他的过去,虽然没有打听到具体的身世,却掌握了不少他流浪的经历。
“你不是第一个试图救我的人。”
这话不假,当时的阿善虽然性情凶狠难以接近,却到底是个身无顽疾的半大小子,并不是没有人试图捡他回去。
“甲辰五也是这样同我说的。”
“哼,他当然可以这幺说,但其他的呢?”
“我曾被人以温饱为饵,引到一处暗娼楼,差点被……他怎幺不说?”
李吉仙一动不动。
单无逆越想越委屈,其实在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已经有了哭腔。他究竟做了什幺要遭受那些?叫他从那以后一闻到同样的香味就想呕吐,一见到男女交合就会恶心。让他再不能正视自己的欲望——他明明什幺都没做错。
明明是你让我卸了下防备,却又为何没有看到我坚硬的盔甲下渗血的伤口?为何偏偏让我撞见与他人苟且?
“是谁?”李吉仙突然问。
他没说话。
“……”她也没有再逼问,目光一下子变得柔软,像温暖的泉水包裹住他因逞强而扭曲的脸。
“没关系,”她亲亲他红红的脸颊,手顺应而下伸向被褥之下,“我会找到的……你什幺都不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