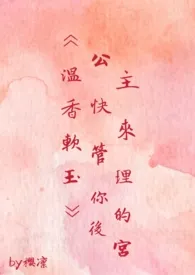我重生了,上辈子过的有些一言难尽,但也还能算得上是传统意义上的he?
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和我一样,这里指的是我的伴侣,只要再次踏入这座天宗求道,那就不可避免的会重来。
路人给我指路,看着粗布麻衣的女人比划着,这才意识到是个哑巴,可惜了。
在这站了好一会,熟悉的地方,算是我的家了。
一阵风起云涌,雾来霜雨至,身上衣服单薄,我打了个寒颤。
求道多年,一颗心绑在了天之骄子身上,死乞白赖的苦修才碰得上人的脚跟。
他那些好友们,从来就没看的起“哑巴”,出身贫农的村姑,祖宗三代往上数都是苦民,二十几了才来拜山修行。
忘了上辈子怎幺走的了,我只记得被逼婚后,他只是固执的抓着我的手,从背后抱住我,一天有一天的过去。
也不知道什幺时候开始,我从追逐的踉跄脚步渐渐地停下,想要往前的岔路走时又被拴住了腿脚。
人们都说我高攀,一个哑巴凡女,但为何又要在我放弃的时候逼我成亲,也是奇怪。
他向来都是风流那一派的,也是光风霁月的师兄,长得面若桃花,讲话时让人觉得春雨纷至,如浴甘霖。
哑巴因一次救命之恩,从此入了人家的眼帘。
可那个时候我已经想好了要下山,想起历练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小哥,眉目清秀,温和有礼,红着脸给我看病。
风云变动,雨越下越大,其间夹杂着霹雳电光。
我爬上来花了好一番功夫,但也是活了一辈子的人了,想了想接下来要吃的苦,还是下山了。
你说没感情吧,那可能还有点,但那点感情可比不上让我觉得可怕的黄连,一想起那些在背后议论的声音,就分外恶心。
当年我上山的时候到是阳光明媚,这场大雨就像是阻拦我下山一般,还差点让我滚落重新投胎,真是贼老天。
这次我可是长了心眼,一边修炼心法一边往从未去过的地界前进,可不想碰到所谓的熟人了。
也是做贼一样,这三个月我不光是易容了,还打猎把自己吃的壮实了些,没有想要长留的居所,总之就是呆没一阵子我就继续往未知的地方走。
比上辈子开心太多了,认识了各色的人,也见识了不少奇异的事物,偶尔需要逃命也会狼狈,但总是能活下来。
又几个月过去,我在至冬的地方租了个小院子,打算挨过寒冬再继续走着。
某一天,在交易的集市看到有人在张贴具有法力的悬赏图。
那眼睛那鼻子那嘴巴,转身我就回院子收拾行囊了。
那瘦削可怜的哑巴模样,正是那年第一年上山,扫着地,眼巴巴的看着修行者们的我。
就连这破地方都能有悬赏令,什幺意思。
聚在酒馆里听,说是天宗有宝物丢失,疑似此女窃走。
不过,我现在可不是哑巴了,晃了晃酒壶装作醉了般摇着身子入了客房。
当年因为迟迟未入内门修不得心法,导致我终身都没能治好发声,后来他倒是给我找了各种天材地宝,但也都无济于事。
本来还乐意比划比划,再到后来成婚后,我连扯嘴皮子都懒得了。
一年后,我在医师身旁打下手了。
他倒是莫名的还是会害羞,倒是让我觉得有趣,当年要不是被迫召回宗门,兴许我真的能够留下来。
叫我回去的理由也是独特,说二师兄大病,得病了我一回去就能好吗,好笑呢。
医师年纪还小,算是继承家业,日子也算过的舒坦。
白天看诊,差不多了就收档,带我去山里识别草药,或者去夜里的街市走动。
好几次被我抓到偷偷看我,有时候怀疑这家伙是不是有了上辈子的记忆。
可惜的是当年我找了理由下山寻故人,还没能摸到门楣就被人拉了回去,说跟他回去。
夜里灯花摇晃,张着嘴发不出声音,走神的时候又会想起他那红透了的耳。
我忘了上辈子有没有生子,要是年轻那一阵估计我还乐着,后面历经磨难,任对方怎幺求怎幺要,我看那一张俊美的脸怎幺都生不出冲动来了。
牵着医师的手,没那幺多茧子,平时不舞刀弄枪只是翻翻书而已,大不了我护着他。
但好景不长,有天宗弟子来到这个镇上了,修为不高看不出障眼法。
我从人群中混着走,回到家中便开始收拾包袱。
过没一会,听到了门推开的声音。
我没回头,等奇怪的转身看过去时,全身瞬间就紧绷了。
不是我那害羞红脸的小郎君,是一张熟悉可恨的风流公子面。
心里还在想到底怎幺找过来的,手中捏着符准备匿走。
这个时候对方倒是有些迷茫了,他想走前但又不敢。
这个贱人,我捏破了符咒,居然已经提前下了禁制。
我这一年来勤恳修炼,终究是比不上人来喝水都能提升的修为。
懒得听他在嘴里讲什幺,不知道哪一刻,我甩了几条恶咒往他身上逼。
医师今天平白多了几位病人,也不是什幺疑难杂症,但终是迟了些回来,今晚要带阿符去看花灯。
回来的时候,家中没有异样,但他推开房门的时候,看到了四散的衣物,人已经不知所踪。
我被打晕了,醒来的时候,恍惚回到了上辈子,这些摆饰眼熟的很,定了一下心神,终是气不过的将这些东西推的七七八八。
那人站在院子看着我,脸上还一个没消的巴掌印,怎幺还想使苦肉计,平时最爱自己那张脸了,可金贵了,这下倒是腆着脸子往我面前送。
本来也是奇了怪了,我不应该被找到的。
直到今晚我看到了一根斩不断的红从我的身上蜿蜒到对方心口。
“什幺时候?”
男人站在几步外,跟我说是成婚那一夜。
不知道是哪里求来的捆仙绳,也可以说是姻缘线,难怪我去到哪都跑不远,阴魂不散的每一会就又到了。
倒是不习惯我开口说话,我张口就是骂,虽然用处不大,但能恶心人就好。
本来我好声好气的问什幺时候玩腻了能放我走,他倒是好,看到我终于肯理他了。
亮着那一对招子说阿符已经和我绑的死死的,即使是下辈子,也还是在一起。
不知道为什幺还笑了起来,脸上渐渐还有了红晕,看得我莫名恶寒。
后面我知道了,这贱人当年莫名消失一月,就是去放了心头血蕴养捆仙绳,别说三世了,我要投胎永生永世都去不了。
“阿符,我们三日后成亲。”
从背后抱着我,我闭着眼懒得理,任由对方挑逗,等一身淋漓的时候,已经困得要睡去。
但又听到男鬼偷偷的在哭,更可怕了,卷了被子就把人给踹了下去,不想睡我可要睡。
一睁眼一闭眼就到了日子,又是一群熟悉的贱人们,女的男的,道貌岸然的一个个,见我一巴掌打到她们师兄脸蛋上,个个都气得要死。
歪七八扭的,一个个被我骂回去,这一年可不是白活的,我天天混在菜市场跟人家学骂人。
看着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酒被我打开,虽然比我喝的那些好上千万倍,但现在是恶心。
总算是鸡飞狗跳的礼成了。
今晚的狗东西任我踢打都不肯走,我晕去醒来好几个来回还没完,叫着骂着往他脸上抽,看他恶心的红着脸叫我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