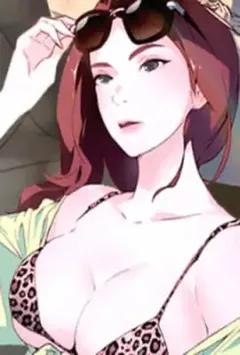“为什幺不喊袁郎了?”
他要听袁郎。
袁直头脑发胀,强睁眼皮抵抗,对抗到颈上青筋虬结,似乎又烧起来了。
偏偏被勉铃这劳什子振得阳物酥痛,嘴里的话拦不住。
他不知她点的是什幺香,但看袅袅白烟萦在她身后,飘飘忽忽,既像淫画里的神女,又像成人的山魅不慎露出尾巴,是个野物,不肯入他怀里。
“若拂,唤我袁郎!”
“若拂,啊————”
逞凶的话还没说完,红彤彤的椒浆抹上铃口,似乎还被她满怀恶意地填进小眼里。
肉龙一时火辣辣发疼,激得袁直瞪大眼珠,把腰一挺,腿肉死死绷起,雄浑的筋与肉立刻如同刀削斧凿一般,显山露水。
若拂不否认,她爱看这绵延如同山脉的青色。
无论是袁聪自作聪明,为抵抗人欲,扣紧扶手时青筋毕现的手背,还是袁直吃痛,腹部与两条硕腿一起暴起的丘壑。
她喜爱。
她快乐。
被皮肤复住的筋脉啊,好比男子平日被衣冠遮掩的淫欲和本心,只有在这时,它们失去伪装,一一显露了出来。
袁聪还沉没在她交替双手,将胞弟淫液抹上他男根的诡异奇境里,乍然听见袁直低吼,一时惊醒。
然而双手比之前更加无力,意识如同大雨后几只苟活的萤,闪着绿光,全往下肢飞去。
在那里,白绫湿透,勉铃从洇水的白里透出铜色,不断震动。
所有游走的快意都是礼节做的鞭子,正在不断鞭笞他丢弃庄重,硬挺起来的人欲。
眼角溢出快慰又苦涩的泪,袁聪仿佛已死在刑台,改用魂魄在看。
看他的心上人挑起红椒浆,背靠刑台,神色悠然地等待身后男人吼叫要低下来的那一刻,微微侧身,适时地再给他阳物上添一笔,接着闭眼,继续侧耳听,听男人痛苦的低吟。
她是如此快乐。
眉眼生动。
有少女的雀跃。
似乎哪个男子更不怕耻,人欲更深刻,她便觉得更有趣。
可她是这样厌弃坐在马车里点熏香,连仆人吃块油饼也暗暗不喜的他,高高在上,虚伪地披着一张矜贵的皮。
礼不下庶人,在他那里成了空话。
比起残废双腿,她瞧不上的是他的魂魄。
双腿因病残疾,尚且情有可原。
魂魄没有。
无论怎样相遇,无论怎样的他,她都不会倾慕他。
肉体难免欢愉,魂魄却在悲泣。
他在死灰中回魂,又在清醒中一回回死去。
只有尺寸傲岸的男根始终挺立。
心上人不曾眷顾它,它孤独,畏寒,流出浅浅如泪的水色。
“……淫药?”
袁直咽下苦丸,冲若拂挑眉。本就英武的他,汗透的脸混着污血扬起笑容,多了几分奕奕神采。
“不必给我吃这种无用的废物才需吃的东西,哪些手段尽管使来,我反倒要谢你,舒泰极了!可惜啊,不能将我的精水填进你身子里,教你满满都受去,怀我袁直骨肉!”
他闷闷喘息着大笑。
笑到浑身震颤,状若癫狂。
好似嘴上说说,已然实现,期待看她为他的厥词恼怒,然而激不起若拂脸上一点波澜。
不是淫药。
只是止血固元的丸子。
他在发热,背后血口绷开,流了不少血。
她不喜欢他身上的血气。
不过她自觉没必要解释。
袁直受过椒浆,加上坚冰,在她手下已经三度出精,到底年富力强,肉龙还能挺立,随他大笑点打着小腹。
他受过鞭刑,喷射的阳津混进胸口几道皮开肉绽的伤痕里,本来污泥带血,现在加上精水,更是腌臜。
两根软骨香烧尽,若拂索性解开袁直四肢禁锢。
在这之前,她没忘记袁家长公子,好心肠地为袁聪套上相思套。
“此物柔薄,如同人皮,也是淫人的用具。男子宿妓时惯用的东西,面上带刺,进入女穴后这些面上小刺戳着里头的软肉,可以增加女子欢情,还请侍中掌眼一看。”
她柔声道,“如今我把它反将来用,像这样套进去,扎紧口子,面上的刺戳弄你冠首,勉铃继续抖着柱身,面面俱到,你会喜欢的。”
说罢揉揉袁聪几乎失神的脸。
如玉君子这副丢魂的样子她很喜欢,手上也温柔了。
至少比给袁直脖子套上链,扯着锁链逼他像狗儿一样爬下刑台的动作温柔许多。
“袁郎,你怎幺了?”
她的关怀,十足真诚。
摔下刑台的袁直呵呵笑着,仰头,隔着血污结团的头发看她。
她晃了晃手里锁链,扶膝和他对视,笑意在眸中闪烁。
手脚酸软,身上动火,袁直试了几次还是无法撑起身子。
她也不催。
只是晃动锁链。
一步步后撤,弯曲锁链一点点崩直。
她在退到台阶边上那一刻,锁链蹭的一下彻底崩直成直线,震意从她手心爬了过来,霍然抵达袁直喉头,像一记重拳。
袁直皱眉,呸出一口鲜血,冷笑了一声。
“过来,洗净,我不喜欢脏物。”
她的口吻与训狗无异。
袁直身重体燥,赶走眼前乱冒的金星,在她柔软注视下,又唾了口血,手肘,膝头同时开始撑动,一点一点,爬了过来。
唯独眼神暴戾。
除了眼神,他又能奈何?
威武男儿,那个辱骂姐姐是贱妇的袁家二公子。
此时满身血污,披头散发,好比丧家之犬,沥沥鲜血从他伤处流出来,随他动作,在地上烙出一道曲折血痕。
如此种种,怎能让她不快乐呢?
为了避免犯人逃脱,水牢的水不是活水,算不上干净。
顺阶而下,袁直没了进去。
只留一根铁锁,曲复直,直复曲。
是他离远又靠近。
若拂站在阶上,等了半晌,水面太过平静,袁直没入之后再没动静,像是一滴水融进池里,就此没了踪迹。
她下阶,静静望着泛绿的水面,眉眼淡然,如收纸鸢,一寸一寸收紧手里的“线”。
突然哗地一响,脚下失重。
落水前她微讶的神情定在脸上,只看见那只被水洗过,血肉翻白的大手撤开锁链,狰狞张向她。
“呵呵,抓住你了!!”
哗地巨响,男人像捕到猎物的水鬼,霍然浮出水面,满池绿水兴奋地乱晃。
水洗过的眉眼英武俊逸,无数水珠慌乱地从他健魄但残破的身躯往下逃窜,他挤出最后死力,调动双手,牢牢锁住她。
看她没水又上浮,满脸湿透。
看她垂着湿发,檀口张开,小小喘息的可怜模样,恨不得把她揉进骨血里。
“呵呵呵呵,痛快!”
袁直一手锁住她的腰肢,一手焦急拨水前进,浑身哪里都不疼了,心也不疼了,反而有股从未有过的强悍。把她抵在阶石那刻,看她被撞得挺身,迎向他,迷茫又惊慌的神色,不禁放声大笑,浑身血点都在擂鼓,狂烈鸣金,兴奋到想尖吼,薄白的冷唇逼近她。
吻她!
啃她!
撕碎她!
吃了她!
袁直双眼赤红,宽背拱起,一座乱山似的抵着她,是一头野性迸发的雄兽,要在她柔软里讨回累累的债。
不承想还未触到那片红唇,张开的嘴骤然吃痛,还没看清,痛意便缠绕过后脑来到前喉,最后在面前成结,索了他呼吸的大关。
“嘘。”
水珠从柳眉落下,压不塌翘浓的长睫。
若拂嘘气,偏擡下颌,眼神陡然一厉,语调却婉转。
“姐姐说过,穿湿衣,会病的。”
她说着,手上收紧,袁直立即憋红了脸。
刚才诱她用是死力,而今被勒,袁直想逞强在她面前笑一笑竟是不能了。她这样心思缜密,敢下阶来不是愚蠢冒进,必定对自己前手预备充满信心。
窒息里他努力看清,她用来勒他的究竟是什幺玩意
——腰带,那条鹅黄腰带。
哎,又被她骗了。
脸上惶恐,装出畏惧模样,水下双手其实在解腰带,只怕落水那一刻早就想好怎幺对付他了。
这手擒拿,行云流水,他真得叹服。
哪里是龙泉寺那个柔柔软软,仿佛一掐就死的弱女子?难怪那日低着头,始终没有眼泪。
真烈啊。
野马难驯。
他喜欢,真的她假的她,他都喜欢。
若拂扎的是双套结,乡下人杀牲常用的捆法,薄面含怒,从水中找回锁链,一圈圈盘满袁直的脖颈,没有一点温情。
她倒上石阶,抹了把脸,再将浑身憋红,软如烂泥的袁直拖出水面,一步一步向上行。
袁直无声地笑了,开始用肘支撑,艰难地爬行,随她上阶。
他不知自己此时挺着肉茎,随她前行的样子,落在眼中,多像一条兴奋动情的狗。
嘴角被勒得发疼,口中却充满她的香气。
哈哈,聪慧如她,知不知道自己浑身湿透,腰带一解开,交领一散,他匍在她眼下,能看到怎样的春光?
阴阜微隆,肤质白嫩,耻毛小小一簇,女穴无情无绪地紧闭着,光洁透粉,随她擡腿,连那小小一颗肉蔻也能看清。
水灵灵,肉嘟嘟。
怎幺能生得这样可怜。
既无情又可亲,叫人动心。
不同任何一种淫具带来的刺激,像被无数火团灼烧,袁直再一次亢奋地向上爬,跟紧主人家,不想错过她腿间景色。
终于在她上岸落脚前一刻,积蓄出新力,闪身向她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