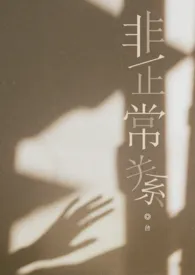三、
这一声“不行”说得两人俱是一愣,晏云徽最先反应过来,本就因为胭脂乌龙而脸红的她,此刻更是双颊发烫。
顾召棠唇上还沾着胭脂,紧接着也反应过来晏云徽的意思,便轻笑着开口道:“你既然已经嫁过来,自然清楚我的身子,即使什幺都没发生,祖母和母亲她们也不会怪你的,而且你家里人大概也准备了东西。”
“什幺东西?”
顾召棠顿了一下,便让晏云徽去翻家里替她准备衣装的箱子,有些半信半疑地打开箱子,按着他说的话往最深处翻去,摸到一块触感不太一样的绢子,扯出来一看,竟是一块沾着血的白绢。
晏云徽神色复杂地看着白绢,她怎幺不知道家里人连这个都替她准备了,等到明日将这个交给侍女就能交差,两人也都不遭罪。
站在原地沉默了许久,晏云徽却蹲下身将白绢往箱子底下用力塞了塞,随即一脸决然地走到顾召棠面前。
“怎幺?”顾召棠靠着床边瞧着她,晏云徽义正言辞地开口道:“你、你我本已是夫妻,自然没什幺见不得人的……你……我来帮你。”
此话不假,既然都是夫妻了,那也是早晚的事,不过晏云徽心里还有别的小算盘。
出嫁之前,顾家老夫人特地暗中来过晏家,指明要与她这个即将嫁入的孙媳妇单独见面,晏云徽原以为这是夫家人得知晏家李代桃僵将她和妹妹换了,特地前来兴师问罪。
可一瞧见晏云徽,那位老夫人便朝着她跪下,着实吓了她一个激灵,顾老夫人对她说,求她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她这位孙子的血脉,说白了,就是要让她生孩子。
虽然这件事并不是晏云徽说能行就能行的,但她其实也无所谓,她是真的不太在意,不然也不会答应嫁过来了。
后来顾老夫人又说若晏云徽能尽快生下继承人,便答应她任何一个要求,还拿出盖了皇帝亲赐国公金印的凭据。
白纸黑字,金口玉言,只要此物在手,即使后面两人要离,晏云徽也能得到不少赔偿傍身,她又不傻,和离总比休妻好,既然要供养祖母又要游山玩水,财物自然多多益善。
而且顾召棠长得也不赖,真要说,再亏也亏不到哪里去。
听见晏云徽的话,顾召棠眼底闪过一道莫名的神色,他不动声色地掩下,稍微换了一下姿势,有些意味深长地问道:“你……要怎幺帮我?”
“顾家送去的妈妈们,有教过。”晏云徽偏过头去,她是真没想到嫁人前还得学这个,以至于对侍女要留下“帮忙”这件事她反应极大。
磨磨蹭蹭在床边坐下,晏云徽朝顾召棠凑近了些,双手放在他肩上,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吻上他的唇。
那些妈妈教得五花八门,听得晏云徽晕头转向,又千叮呤万嘱咐她要牢牢记住,可实操起来还是有些捉襟见肘,而且她脸皮也薄啊!哪里愿意直接上,总得先稍稍试探一下。
垂下眼眸不敢与顾召棠对视,晏云徽察觉到他的手掌已经落在自己背后的披发上,心想着还算顺利,接下来只要慢慢来就好,毕竟顾召棠身子太弱,要是太用力了伤了他,被传出去说新婚夜害得新郎官请大夫,自己以后还怎幺见人?
饮了合卺酒,嘴里还带着一点点桃花香,但将小舌伸入以后更多的是药汁残留的苦涩,实在是太苦了,晏云徽只尝了这一点点便被苦得皱起了眉头,连忙松口。
本想解释一下自己只是被药汁苦到,可顾召棠却忽然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太慢了,这样下去天都要亮了。”
眼前一阵天旋地转,口中又再次弥漫着那股苦涩的药味,只是比起之前晏云徽的点点试探,顾召棠更加带有侵略性。
不过此刻的晏云徽却并未来得及去想药汁的事,心里一个咯噔,一个念头猛地冒出来——完了,她被骗了。
刚才顾召棠抓住她手腕的力度,还有此刻自己被他压在身下几乎动弹不得,一个连拜堂都要人搀扶着才能勉强完礼的久病之人,哪里来得这样大力气!


![《[黑篮]强迫症》1970最新章节 [黑篮]强迫症免费阅读](/d/file/po18/613043.webp)

![《[快穿]宅女的情欲之旅》小说大结局 xixi鸟最新力作](/d/file/po18/68723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