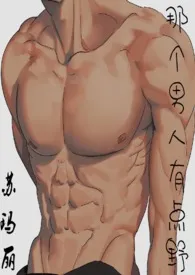自那天西湖柳莺里,时安两家以亲家的关系把话说开后,时律去大院的次数更加频繁。
外人眼里,时律早已是安委内定的女婿,在院里碰到的时候,都会热情的与他打招呼。
过去他爸时韶印没退居二线那会儿,跟安康升属于“对家”,存有竞争关系,如今快成亲家,过去的纷争也算是烟消云散。
身为一名历史老师,安卿对官场更是早已看透,她熟知千百年来,都有一个从未变的规则:没有永远的敌人,有共同利益的时候,敌人也可以联盟成为盟友。
她爸安康升,时律的父亲时韶印,此时也正是因为某种时局的变动,想要快速促成她与时律的姻缘。
又经过一个月的相处,两家正式会面,由孟老当开话人,提议这个春节前把俩人的婚事给定下来。
来前时律跟安卿通过话,征询过她的意愿,她还如下午茶那天通透:“那就订呗,反正早晚都得订。”
于是,在西湖国宾馆的这个飘着小雪花的夜里,安卿与时律的订婚日期定下了——大年二十八。
大年二十八:做馍,贴年画。
安卿心想:可真会选日子。
跟时律在湖边散步的时候,安卿擡头看了看不远处半山上的雷峰塔,又扭头看了看身边始终沉默的男人,“在等你的白素贞?”
时律自然是听懂了她这句话的言外之意,走了几步后停下:“我比许仙还窝囊。”
许仙至少为了白素贞敢与法海抗衡,不像他,连抗衡的机会都没有。
安卿改了口问:“梁祝?”
这次时律笑了,“梁山伯和祝英台是殉情。”
“你们有没有想过殉情?”话问出口,安卿意识到自己唐突了,“不好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
时律没半点反感,反问她:“你这姑娘是不是从没恋爱过?”
“跟你相亲前一周刚分手。”她也没再藏着掖着,“追了我快两年,从北京追来江城,我以为是爱情,结果是想吃绝户。”
“怎幺发现的?”
“他跟他妈妈的聊天记录被我看到了,他说他受够了当舔狗,他妈安慰他,只要把我娶回家就不用再供着我了,让他再忍忍。”
说这些话时,安卿始终在笑,没半点伤感,就好像在讲别人的事。
时律跟她说:“是他不配。”
“……”什幺不配?安卿满眼疑惑。
“他不配当你的舔狗。”
这话把安卿成功逗笑,她仰起头,习惯性的捂住嘴笑。
长卷发被风吹乱,小雪花落在她眉心处,身后是西湖,左前方是亮灯的雷峰塔,她穿的还是新中式的盘扣大衣,格外的好看。
笑了会儿后,安卿一本正经的点头:“我也觉得他不配。”
几缕碎发被风吹的黏在她唇瓣上,察觉到有脚步声靠近,时律擡手帮她把碎发拂去,又温柔的从她口袋里掏出来发绳,帮她把长发给扎起来。
时律的掌间有股淡淡的茶香味,好闻到让安卿忘记了他们是在“演戏”。
尤其是在被时律牵住手,继续往前走时,温度透过掌心传递,她心间突然荡起不该有的涟漪。
仅几秒,安卿便将这种涟漪压制下去,在离那些人远些后,她主动将手收回,手机好巧不巧的响起振动声,是她那不配当舔狗的前男友。
陌生号,还是北京的,一开始她还会接,次数多了,每次都是那个男人换的新号,这次她直接拒接,再次拉黑加入黑名单。
见她这般决绝,时律想起回忆中的那个姑娘,因为那姑娘跟她一样,决定舍弃一段感情时,绝对不会再给对方留一丝一毫的机会。
一个小时后,时律推翻了自己的话。
安卿比那姑娘还决绝。
大院门口,京牌的黑色迈巴赫停在梧桐树下,雪已经下大,前男友就站在车旁,安卿连看都没看一眼。
没有通行证,警卫员是不会给外来车辆放行的,能明显的感觉到那男人在咬牙切齿,透过后视镜看到他一拳捶在身后的车身上,时律不免猜想:他是懊悔失去了安卿这样好的姑娘?还是懊悔没有再多忍段时间?
因为他妈高越也曾跟他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再忍忍,把卿卿娶回家,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没错,时律的任务就是完成跟安家的联姻,把安委的这个独生女娶回家,两家共赢的基础上,也为他未来的仕途添砖加瓦。
有了这种认知,每次看到安卿眸底的那抹暖笑,时律都觉得是种暗讽,暗讽他也不配。
所以在驶进大院后,时律没着急下车为安卿开车门,把车停在巷口,沉声问她:“要不要再给他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