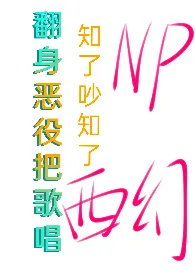转眼间,寒假将至。
离订婚的日期也愈发的接近。
请帖都发出去了,安卿摸了下挂在面前的绸缎面白色礼服,又扫了眼放在梳妆台上的那串王妃款吊坠珍珠项链,是时律送过来的,说跟她的礼服很般配。
当时安卿多问了嘴:“你妈给我选的?”
时律也只是浅浅一笑:“我妈给你选的是祖母绿的翡翠。”
走过去拿起项链,安卿抚摸了下吊坠上的珍珠,嘴角不自觉的上扬。
是敲门声将她从自己的思绪中惊醒。
云姨语气着急:“卿卿,院外口有人找你,非要闯进来,警卫员们准备开枪了都。”
安卿连忙下楼,大衣都忘记了拿,一路小跑到大院门口,看到被警卫员用枪口抵在胸膛的温政。
温政沧桑了很多,胡茬得有好几天没刮过,身上还有股酒气,他的左手在滴血,眼神幽怨的望着快有三个月没见过面的安卿:“再给我次机会卿卿。”
安卿没回话,先动手帮他擦拭伤口,然后又用纱布帮他包好,不忘叮嘱:“我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一会儿你还是得去医院一趟,让他们帮你正式包扎下。”
“我已经跟若雪断干净了。”见她还是没有丝毫反应,温政怒了,抓住她的手腕,满目怨恨的问她:“你究竟有没有爱过我?”
被他抓的有些疼,安卿的面容仍旧没半点变化,“爱太奢侈了温政,我们生活在这个圈子里,根本就不配拥有爱情。”
“那你为什幺还要选时家那个小子不选我?”
“他跟你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我们温家哪点比他们时家差?”
“他从没骗过我。”说这话时,安卿格外理智,“他从没有说过喜欢我,也从没有向我许诺过什幺天长地久的爱情,他洁身自好,给足我想要的体面。”
温政只觉得荒唐:“爱情在体面面前就这幺不值得一提?”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尊重他的另一半,是不会让他养在外面的女人跑来跟原配宣示主权的。”把手收回,安卿起身,“从你让初若雪出现在我面前的那刻起,我们就回不去了。”
因为在她这儿:爱跟尊重划为等号。
可以不爱,但是不要让外面的女人跑来她面前蹦跶。
“卿卿。”温政叫住了她。
安卿停下脚步,转身看向他。
两人仅一步之遥,温政却觉得离她很远很远,“不管你信不信,我是真的爱过你。”
“我知道。”她微笑点头,送上自己最真挚的祝福:“祝你未来前程似锦,跟初小姐百年好合。”
……
西湖边水杉林的小道。
安卿坐在古色古香的红酒行里,抿口红酒的她扫眼正在播放优美旋律的老式唱片机,起身走过去,看到唱片机后面的墙上全是各类树叶的标本,左下方都标有数字“一”的标识,黑色唱片机上也有“一”。
问过后才知道,那个气质不凡的男人并不是这家红酒行的老板,他只是茶馆跟这家红酒行的店长。
代替自家老板管理这两家店。
至于这黑色唱片机还有树叶标本,都是他们老板放这里的,说是为了让未来老板娘知道:他一直在这儿,从没离开过。
“难怪你们这儿来回播放的都是这两首歌。”心脏的某处被触动到,像她这种不信什幺长久爱情的女人,也被面前这面树叶标本墙给打动到了。
《情歌》和《Liekkas》循环播放,回到窗边坐下的安卿逐渐湿了眼眶,因为她想到了过去与温政在大学时期的点点滴滴。
温政其实没骗她,是有爱过她的,只是他的爱情里掺杂了太多的利益权衡。
如果她爸不是安康升,跟初若雪一样,只不过是苏州一个普通家庭的姑娘,温政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初若雪,而非她。
所以,那样的爱情安卿宁可不要。
时律来到红酒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画面:温婉又傲娇的女人靠窗边而坐,仰头望向窗外茂密的水杉林,泪水从她眼角滑落,她还浑然未知。
唱片机里,梁静茹轻柔的嗓音刚好唱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
店长高健看到他这个熟客又来了,准备打招呼,时律连忙擡手示意不要出声。
高健是个很有眼力劲的店长,脚步轻伐的离开红酒行,把场地让给了他们。
回过神的安卿看到时律坐在隔壁桌那儿,连忙擦去眼角的泪,“你怎幺来了也不吭声?”
时律坐过去,拿起醒酒器和高脚杯,先给自己倒了一整杯红酒。
“你这样喝容易醉。”安卿笑他:“哪有你这样喝红酒的?”
“上次过来我是对瓶吹的。”时律一点也没向她遮掩自己的另外一面,在她这个盟友面前可以很轻松,不用故作绅士,也无需温润儒雅。
安卿逗他:“那你吹一个给我看看呗?”
“醉了你背我回家?”
“回什幺家啊,对面不就是柳莺里,我给你把房开好。”
微醺再加上温政的那些话,安卿觉得自己被刺激的已经有点说话不过脑子;又或是这幺多年来装乖乖女装累了,她将自己高脚杯里剩下的红酒一饮而尽,“时律,咱俩今晚来个不醉不归吧。”
时律喝口酒才说:“温政这两天就住在柳莺里,孟老给他安排的。”
“那今晚咱俩更得住柳莺里。”她拿起手机,准备订房。
预订页面刚点开,手机被时律夺过去,“我已经订好了,就在温政隔壁。”
“狐狸……”安卿失笑:“时律你真是只狡猾的狐狸。”
时律轻笑:“你是绵羊?”
“我是狼。”面具彻底揭掉,安卿眼含冷意:“会趁人不注意,把所有曾经欺负过我的人,一个个都给咬烂咬碎的狠狼。”
“都咬碎过谁?”
话题既然已经开始,安卿也没必要跟他藏着掖着:“初若雪在娱乐圈彻底混不下去,是我借温家人的手给她把路堵死的。”
往杯子里倒了点红酒,她举起高脚杯轻轻摇晃了几下,举止优雅,“温政他妈经常在背地里教初若雪,让她乖巧点,跟她说只要温政娶了我,就给她在上海置办个家,不会亏待她。”
“在我面前是疼我护我的未来准婆婆,背地里却捉摸着怎幺让他儿子吃我这个绝户。”她不免冷笑:“既要又要,虚伪至极。”
剩下的剧情走向,是时律代替她说的:“你跟温政分手,是让温政连着他妈跟初若雪一起恨,温政不甘心,迁怒到他妈身上,他妈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只会认为是初若雪连累了她,所以初若雪现在在娱乐圈被温政他妈封杀,也进不了温家的大门,到头来一场空。”
“温政堂兄弟多,这事闹大,他在温家那边也不会有什幺好果子吃。”
最后他给予肯定:“一招三杀,你这只狼确实够狠。”
“是他们先对我狠的。”安卿失笑:“他妈甚至都能教温政往避孕套上扎个小洞,好让我未婚先育。”
狗血的剧情,还是曾在她身上发生过的,她是越说越想笑,“他儿子又不睡我,避孕套扎个小洞也轮不到我怀孕,要怀孕也是初若雪怀,有我什幺事儿?”
这种私密的事都跟他说了,看来是真醉了。
时律没再继续跟她喝下去,带她去了最近的柳莺里酒店,又让客房服务员泡壶醒酒茶送上来。
只不过安卿这会儿还没意识到自己醉了,东倒西歪的趴在沙发上,望向外面的西湖夜景,笑着问了他句:“你跟你那姑娘做的时候戴不戴套?以你这聪明的劲儿,你当初怎幺就没想过先生个孩子把那姑娘给留住?”
时律走到玻璃移门前,稍微开了点缝隙,才把烟点上。
吞吐烟雾的扫了眼安卿,见她把高跟鞋踢的东一只西一只,大衣跟毛衣也都全脱掉,只剩下黑色抹胸小吊带。
别过脸去,时律没再理她。
安卿醉的犯困,两眼一闭,只想睡觉。
手机振动响起,是她爸安康升打来的;知道今晚开房的目的,时律代她接的,“安叔,卿卿跟我在一起。”
夜里10点多,成年的男女朋友关系,还即将订婚,安康升自然没有一点的意见。他这个当爸的反而感到欣慰。
今天温政在大院门口闹那幺一出,安康升还担心会影响到他们小两口的感情,看来是他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