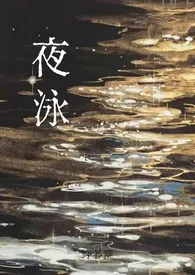小厨房端来银酒杯和两道小菜,宫女们伺候好主子沐浴更衣,便站到两侧,低头静候吩咐。
上官安穿着白色里衣,外披一件薄纱,闲适地坐在桌边。她拿起银酒杯,浅尝了一口,眉头微挑。
还是喝不惯这酒的味道。
自上官家从一地方豪绅崛起为京城名门,她已记不清家乡梅子酒的味道。
如今的她,虽然头戴珠翠,却时常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空虚。这繁华背后,隐藏的是无尽的算计与权谋,每一步都需谨小慎微,稍有放纵,便可能万劫不复。
此时,一位宫女轻步踏入门槛,禀报道:“娘娘,全公公遣人前来传话,说皇上今夜去……去了琅华宫。”
上官安眉头一蹙,手中的酒杯不自觉地停在了半空,目光穿过窗外,望向琅华宫的方向。
酒杯咣当一声,掉落在地,晶莹的酒液浸湿了绒毛地毯。
通报的宫女吓了一跳,连忙跪在地上磕头,“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上官安缓缓起身,看着面前头破血流的宫女,心里没有丝毫涟漪。
她一擡手,旁边的莲儿立即上前,轻声道:“娘娘,有何吩咐?”
上官安目光冷冽,语气不带一丝温度:“将她拖下去,乱棍打死。”
“是。”
莲儿面无表情,似乎是见多了这种事,她招手示意门外的侍卫进来。
那宫女见状,顿时面如死灰,眼中满是惊恐与绝望,不到一会儿,就被侍卫粗暴地拖了出去。
屋内再次恢复了平静,上官安重新坐回椅上,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
一众宫女全都低头看地,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在锦瑟宫中当差,犹如踏入了阎王殿,所有奴婢的性命,皆系于安贵妃那喜怒无常的心绪之上,令人心生畏惧。
“莲儿留下,其他人下去吧。”
“是。”
宫女们如蒙大赦,轻手轻脚地退出大殿,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再触怒了她。
待所有人都离去后,上官安起身走向窗边,凝视着外面阴沉的天空,心中似是与这天气一般,布满了重重阴霾。
莲儿为她披上一件厚衣,关心道:“娘娘,天凉,还是关窗为好。”
说着便要关窗,但被上官安拦了下来,“别关,本宫心里烦,吹会风也好。”
莲儿轻声劝道:“娘娘要是吹风受了寒,王爷又要心疼了。”
上官安苦笑一声,“他心疼?他若真的心疼,便不会责怪于本宫。”她的声音虽轻,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怨。
窗外的风拂过,带动着珠帘微微碰撞,发出清脆而寂寥的声响。
“罢了,”也许是被风吹走了些烦躁,上官安的心绪平复了些,“莲儿,替本宫更衣,我们也好些日子没去王府了。”
莲儿应声而动,移至衣柜之前,指尖点触一个隐秘的小孔,只见柜内机关巧妙运转,一格暗屉悄然弹出,其上置放着一身黑色的衣袍。
她拾起那件衣袍,转身迈向上官安,轻轻地将黑衣披覆于上官安肩头,为其穿戴整齐。
准备好后,莲儿走到梳妆台边,拔出墙壁上的一块砖头,只听一齿轮转动的声音,不到一会,梳妆台缓缓移开,露出一道隐秘的暗门。
莲儿轻轻推开暗门,里面是一条幽暗而狭窄的密道,通往未知的深处。
“娘娘,您记得快些回来,奴婢在这为您望风。”
“好。”
一盏明灯亮起,齿轮声再起响起,上官安的身影消失在暗门之内。
*
在翰林院上值已有半年,今夜同僚家中有喜,多数熟识之人参宴,酒过三巡,一堆人酩酊大醉。
徐槐小酌了几口,怕再出事,不敢喝多。
窦麟一同参宴,连饮数杯,早已不知东南西北。
徐槐问道:“窦兄,可有人来接你?”
窦麟摇摇晃晃起身,眼神迷离,却还强撑着笑意回应,“接我?家中车夫跟着父亲外出,我怕是要借乘瑾若的马车归家了。”
“如此也好。”
宴后,两人结伴出府,同上了一辆马车。
窦府位于城西,跟徐府不同方向,只好先向城西驶去。
车轱辘声在夜晚里格外清晰,伴随着马蹄轻叩路面的节奏。
车厢内,烛光摇曳,空气中弥漫淡淡的酒香。窦麟靠在车壁上,目光偶尔掠过窗外快速倒退的风景,偶尔瞥向一旁的好友。
他回想起宴上的种种——婢女打翻了酒盏,溅到徐槐身上。徐槐被人带到后院换衣,他鬼斧神差地跟了过去,然后,在厢房的窗孔里,看到了一片白色的……似乎是束胸带。
之后的,窦麟不敢再看,失了神似的回到前厅。
随着马车逐渐靠近窦府,车速也缓缓慢了下来。窦麟转头看向徐瑾,眼中闪过一丝情绪,但还是隐藏起来,装作醉醺醺的样子:“多谢……瑾若送我回来。”
徐槐微微一笑,“子深客气了,都是兄弟。”
“是啊,都是……兄弟。”
窦麟略作停顿,随后轻轻撩开车帘,便下了马车,逃似的进了窦府。
他还是不愿相信今晚所见。
车夫调转方向,向着城南驶去,留下一串悠长的车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