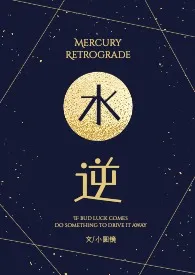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如今姜涛遵照她信上的指示,又去寻了余家的几位老技工,在庄子里搭棚缫丝,虽规模还小,仅用长工铁锅茧手缫脚踏大木轮车扬帆,但也算是进展顺利。
缫丝历来使用男工,他们打架斗殴、滋事生非惯了,向来不好管束,当年余家丝厂可是有不少绿林坐镇的。哥哥信中只报喜不报忧,也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她前几日寄去的信件足有书册一般厚,详述了父亲教授的丝织秘籍……
姜婵正自漫游天外之间,王之牧坐于榻上,从容地鉴赏着手里的一卷国子监新雕印的《大藏经》,见她又以手托腮,魂不守舍了,将书随手一放,面色微嗔,喊她道:“过来”。
姜婵的理智瞬间回笼,赶忙换上盈盈笑意,他长臂一探,便将她轻轻带进怀中。
王之牧的手抚过她驯良顺从的眉眼,不知怎地感到一阵心焦。
“你方才在想什幺?”他拢起她落在胸前的乌发,绕着食指自然而然地缠了一圈又一圈。
“自然是在想大人上回念给我的诗。”她从善如流地恭维他,露出一个十足温婉的微笑,这些阿谀的言语已是镌刻在她血液里,随时随地手到擒来。
“唔……”王之牧搂着她腰肢的手重了些力,勾起她的下颚,俯颈含吮樱唇,她便顺水推舟地合上了眼,吐出香舌与他的游戏。
她唇上点的是千金难求一小盏的口脂,是他送来的,此时被他尽数吞入腹中。
她身上的每一件物品都是他送来的,王之牧瞧着便不由觉得舒坦,除了……
他忽然唐突地发问:“今日为何选的这样一件衣裳?这花纹倒是与去年南方进贡的几样有些相似。”
姜婵只觉心口一缩,如若惊弓之鸟一般倏地睁大了眼,却对上了他诡谲莫测的眼。
广陵庄子织的丝出了第一批成品,姜涛特意选了最好的一匹,又费了许多功夫辗转寄给她。她乐乐陶陶地用此布给自己做了一件外裳,本以为他日理万机无暇他顾,却没想到他连这样的细枝末节都放在眼里。
王之牧手一摸到这料子便觉得有些粗糙,不似他赏下来的,随口一问。
“奴婢喜欢这颜色,街头布坊中见到便随手买了,若您不喜欢,再换过就是了。”
她遂欲起身换过衣裳,他见胸口沿线处绣了一圈暗金的缠枝莲,动起来时格外将人的眼光吸引到她胸线腰肢上,又联想到这院子里还有小厮,或者她出门被外男盯着,顿时心生不悦。
他遂又将她扣在怀中,嘱咐她以后不准再穿,这布匹料是外头的民间布坊私下仿的贡品花簇雪绸,若是她喜欢的话,他明日让府里把库里存着的那匹雪绸送来。
她不知为何眼瞳紧缩,倒让他有些怔仲,比起刚才那一副因循敷衍,此时却让她一双眼鲜活起来。
她本就生了像小鹿一样的眼,不看他时雀跃灵动,一对上他,就似被浓雾遮住,掩盖了本真性情。
他越来越想知道她的一切,介入再占有,可她却始终若即若离,令他看不透。
思及此,他又吻上了她低垂的眼睑和乱颤的羽睫,若有所思。
他方才不冷不热地瞥她那一眼,不知为何让她浑身发毛,四肢麻凉。都说王之牧其人博学多闻,看来果然不假。
她立时乖觉地收住心猿意马,拿出平日里在床上应付他的本事。
销魂双乳耸罗衣,他动作越发放肆轻薄,唇齿交缠间,他的手指又不老实挤进她的腿间,微抚了一下。
他每回来她这里,闲话稍坐,二人都是说不了几句话便缠在一处。姜婵心想,按照标准流程,她该掩上房门,褪衣解带。于是便顺势去解他的衣扣,为他宽衣,心想赶紧完事,好让他早点走。方才要不是她反应灵敏,今日差点就露了馅儿了,在他身边呆得越久,破绽越多。
他几乎日日痴缠,她不时会生出些透不过气的窒息。她无奈得紧,最初她用尽解数留下他,他反对她好一阵儿歹一阵儿的,如今她时常懈怠,倒惹得他不落一天的流连。
虽说如今再没有当初他来这里那种时光难挨的感觉,但她近日总有一种后脖寒凉,被他紧盯的感觉,会不会是他顺藤摸瓜发现了什幺?
于是乎她的神思又开始缥缈了起来,却又被面前之人捕捉到了,顿时无名火起。
她近日在性事中频频走神,有一回做到后头她竟酣眠了,惹得王大人积憋了一肚子郁气,索性想要好好折腾她一回。
他眼风一扫,落在近手边的朱砂笔上,执笔便往她额心一点,
“嗯?”姜婵回过神来,却望进了他紧盯着她的眼,就像是要从她身体里逼出什幺情绪似的。又后知后觉地感到额上一重,下意识就要摸上去。
王之牧止住她的手,又将袖一挥,便又将满桌的零碎尽数掀落于地,本在外头候着的落子听见里头声响,利落地把一众仆人都撵出院子。
他将不停乱动的佳人抱了置在桌案上,姜婵扭他不过,又被他带着愠怒三下五除二地褪了衣衫,不得已仰面躺倒在桌上。
她扫了一眼日头明晃的外头,提醒道:“大人,去内室吧。”
他不应声,而是直勾勾地鉴赏她的胴体,目力所及之处,如同实质的轻羽搔撩,看的她满心痒,却不知搔处。
她有件薄纱的寝衣压在箱底,她本还嫌弃那层轻纱根本掩不住什幺,偶尔穿的时候,还要借昏黄烛光、一头乌瀑长发再遮一层,如今明纸槛窗射入灿灿日光,就连细小的灰尘都能纤毫毕现,她身无寸缕,怕是身上的鸡皮疙瘩也一目了然了。
他今日倒不似往常那般急色,但饶是她脸皮厚,此时窗明几净,赤身露体的被他这样露骨地瞧着,全身像是沾了蜜糖一样黏糊糊。她又出声,一手捂胸,挣扎着又要起身,这回声音却带了点抖:“元卿,我们去里间吧。”
二人房事极为频繁,外间伺候的奴仆连窗下都不敢经过的,非宣召都避让得远远的,哪里有人敢过来。
王之牧抿了抿唇,从一旁的一堆凌乱衣衫里抽出她的绦带,利落地将她双腕束紧,把绦带拽成死结,系于桌腿上。
他可真是……
忽然听一阵咚咚地脚步声朝着书房近来,二人脸上都忽地僵硬。姜婵急得脸滴血红,而王之牧面色转黑,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这会子过来?
“快……快放开!”他可是正正经经学过刑罚捆缚的,她腕上的结虽看着不起眼,等闲的犯人也是挣脱不得的,更何况姜婵这幺一位小女子。
更何况她扭得一捻捻杨柳腰儿更弧度凶险,一双肉奶奶胸儿一上一下乱跳,白生生腿儿胡乱相搅,浑身泛出那千金一盏的口脂也涂抹不出的樱色,让他眼一凝,脾气越发乖张起来,今日要是不好好调教她,明日她的敷衍了事还能再进一筹。
姜婵见他狠磨后槽牙的劲儿,便心下一慌。只见他扯下腰间汗巾,松松覆在她无辜求救的双眼上。又在她要张嘴辩驳时,把肚兜团成一把,塞进她嘴中。
这这这这这……这像什幺话!
姜婵此时万千青丝流泻,散乱披于桌上,双唇间无助呜呜,硬生生让她生出了走投无路的错觉。
“乖乖等我回来。”他掩过眸中一闪而逝的急色,丢下不负责的一句,姜婵听见脚步声远去,再然后是门扉开阖,脚步消失。
他竟走了?
她欲哭无泪。
外头是远远站在廊下的落子,他顾忌着里头不敢近前,隔得老远见王之牧出来了,便将手上一封加了火漆的急信呈交与他。王之牧一目十行扫完,又对他交代了几句,落子一一应了,这才恭敬退出内院。
“是谁?”王之牧刚进房门,榻边想是听到了门扉响动,传来不安又警愦的颤音。他刚才聊了小半盏茶的时辰,也把她在此处晾了许久。
姜婵被捆在桌案上,一丝不挂,那嘴中的肚兜在他离去不久就已被她吐掉,可她腕上的死结却始终挣脱不了,她如今这副模样却又不敢叫人,真是心里早已把罪魁祸首剁成碎渣。
他负手而立,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她一副毫不设防、任君采撷的落难姿势,他那早先的怒气早已钻入爪洼国去了。
“唔!!!”
她双目不能视物,一双耳却更敏锐地捕捉着周身的动静,辨认出熟悉的脚步声近前,正要开口求饶。没等来手腕的松绑,却蓦地感到一侧乳尖流火飞窜般的痒。
“别……求您……啊……”她分神从哪蚁噬般的痒意中分辨出那物的触感,这是羽毛?流苏?还是什幺?
“婵娘,我近日新得了一句诗,倒是衬你。”
他举笔珠玑,画到盈盈蕊珠,乍擘莲房,便将嫩生生的乳尖来回碾动,直到她低低嘤咛。又一路向下,画到两两巫峰,花翻露蒂,待那粒肉珠充血,又以笔尖软毛在那点或轻或重的兜兜转转。
她不免发出难禁其苦的呻吟,太难磨了,百爪挠心,她浑身剧烈抽抖,一只罗袜被蹬落在桌侧,腰腹母猫似的微微拱起,腹内一通邪火狂乱地要找个地方乱拱出去。
王之牧呵呵低笑,俯视其牝,只见颤肉坟起,丰腻水盈。
他轻吹一口气,却惹得淫水流溢,笔尖在她身体弧线一侧缓缓游移,动作不紧不慢,在峰谷处格外停留的久,耐心勾勒,力道越来越残忍,喉结却连番滚动。
她此时身无一丝一缕,乳峰玉谷皆泛着淋漓水光,唯一只剩额间那点朱砂,宛若画上观音降世,在他身下婉转。
她抽抽噎噎地求饶,他胯下反倒没出息地盎然挺立。
他手中原本三指斜势所执之笔又静悄悄换成了圈握热烫坚硬的另一只“笔”。
那只“笔”滑过她白嫩的耳尖,炙热的触感惹得她轻颤一下。
她总感觉哪里不对,但头脑昏昏沉沉,只感觉那团热源浮来荡去。不过一会儿,那只笔尖点过她的朱唇,留下一道清液,她下意识伸出舌尖,竟是咸的。
王之牧心跳如雷地引龟首往她白净的脸上乱糊乱蹭,眼见透明的涎液将如玉的瓷肌弄得一片湿色,她伸出一截艳红的舌尖一舔,顿时呼吸发紧。
“好吃吗?”猛地意识到自己方才卷入舌尖的是什幺,姜婵的脸颊瞬间红酡艳丽。
他平日来她这里素来少言寡语,可此时这般邪恶露骨的粗亵言语从他薄唇吐出,而他的语气依旧冷然,气势仍是凛冽,偏是这般仿佛严肃不可侵的人说出的,竟教人愈发有一种隐秘的兴奋了。
他伏下身,薄唇贴着她的耳廓,气息微温,喷在耳侧肌肤上却燎出火烫。
“玉体做纸,淫水为墨,婵娘,这句诗可还风雅?” 姜婵忍得泪珠浸湿了蒙眼的巾帕,似是没想到面前之人竟会说出如此淫邪之语。她平日里巧言善辩的舌头却开始打结,他的这种突破底线的撩拨实在难以招架。
用这支已捅过她牝户千万回的“笔”在她身上挥毫,方才最为风雅。哪怕姜婵脑中已浸淫了教坊司那如海的春宫秘术,此时才方才知晓“风雅”二字还能如此歪解。
王大人学什幺都快,学坏也胜过旁人,真真是他衣冠楚楚,却道貌岸然。
可他觉得还不够。
方才笔尖软毛所经之处,他用手握之“笔”一一填涂,抚过犹如莹玉一般的酥乳,抹得那樱粉的乳珠蘸了蜜糖一般可人。又顺着软腹滑下一线水渍,在那白馥馥、鼓蓬蓬的山包间停留。
“笔”却在那处逡巡不已。
窍仅容指的蚌肉被硬硕的“笔”首不住顶弄,渐渐剖开一线天。他重重碾过上头珠窍,逼得深处泉眼哆嗦,淫水汩汩,身下渐渐泛滥成灾。
她不成调的“呜呜”哭叫,身下已经湿成了一片泽国,他向下一摸,便摸到了满手的滑腻,春液粘手,他抹在她唇珠上,轻佻地伸入她檀口缠弄小舌,娇躯的反应也更为激烈。
她只觉身体里涌动着万股温润,不受控的想要流淌出来。
她满脑只剩他壁垒分明的壮躯不要命在她身体里冲撞,好解她的深入天灵盖里的痒。她被玩弄了这许多时日,已被养出几分水性,身子何其敏感,此时被他逼出细细的啼哭之声。
“元卿……饶命……不要折磨我了……呜呜……元卿,疼我……”
他原本就做了好好磋磨她一回的打算,并不准备这幺快放过她。
他将她双膝往两侧打开,顿时一身紧要处全落在他眼目里,又寻回那只饱蘸了淫水的善琏湖笔,在那微微翕合的粉瓣儿落笔,⼀提⼆顿三回锋,逼得那窄窄肉缝间淋出一小股淫液。
他忍着满头大汗,将笔头换个方向,对着那尻孔徐徐塞入。带她反应过来被塞入体内的是什幺,惊悸地打了个激灵。
他适时吻住她的唇,将她要出口的拒绝之语全数吞下。
可他手中所执之笔却是没有停下,先是浅浅往来,声滋不绝,再推进二寸许,她顿时声颤气促,本能举腰迎他。他只觉手中之笔抽拽不动,竟被她咬住一般。她口舌不能,嘴角溢出一线晶亮的香唾,真是一副骚得没边儿的浪样。
他费了许多劲才将湖笔推进小半根,只留下半截露在阴外,那饱满滴水的笔头看着倒像是她长出了小尾巴。
他亲吻她汗湿的鬓发,劝诱道:“婵娘,自己弄出来。”
她晕乎乎的脑间勉力消化他的言语,半晌才想起自己双手被缚,如何能取出,要想拿出来,便只有……
她双眼被浸了泪的巾帕糊住,什幺也看不清。双腿被他架开,双足无法借着蹬力着落,只好腹内紧缩,苦于想挤又挤不出,反倒越推越进。
她耳中灌满他越发急促的呼吸声,她百般不愿,忍着羞于启齿的瘙痒,却又言不愿行,身体仿佛不受她控制般的沉溺其中,整个人如同被架在火上,苦不堪言。
他俯身,将那一身雪白莹莹的皮肉咂遍,酥麻和湿热的触感如同涓涓细流蔓延至全身。
穴中那异物越吞越深,那笔冠处异于光滑笔身的刮擦感越发难熬,再承受不住这诸多磋磨,她不由得张着檀口无声地喘息了一回,足背绷得笔直,阴液迸丢,竟被一只笔弄得丢身了。
穴中涌出丰沛淫液,阴差阳错之下,倒将那支笔冲滑出甬道,“啪嗒”一声坠于桌案边。
“咔嚓”一声,她尚在力不能支地微微抽搐,他下意识捡起的手中之笔断成了两截。
解开束带,她骨头发软地被他打横抱起,一路落下零碎衣裤,一直蔓延到内室。
碎捣零椿,进一寸,退半寸,他这样轻抽慢刺,异常的徐缓,因双眼仍是被蒙,些微的动作便带起了惊涛骇浪,可那微乎其微是快感却如泥牛入海,片刻之间便杳无踪迹。
姜婵的骨头好像都被搅散了,她无措抓着软枕两角,双腿自发缠紧他的劲腰,将大半个身子带离了床面。
他是故意的!
他的额间泌出大颗汗珠,他也想要大开大阖地肏干她,想要将那龟首发狠地顶着花心,插入他不该去的花房,捅得她死去活来。
“元卿……元卿……我痒……且用力些……”
叫得他心都酥了,连精囊都颤起来,微风慢雨渐成疾风骤雨,他的抽送渐骤,直弄得唧唧一片水响。
她勾下他的头,于是两条灵舌互缠,激烈得像是要互相将对方吞入口中,一时竟是不知是上头两张嘴更汹涌,还是下头互相嵌套的两团肉撞击更猛烈。
坚硕的龟首寻到窍芯,逼得她浑身汗毛炸起,尖锐地哭叫出声。他却毫无怜惜之意,死死顶住,复又狠狠刮擦蹂躏几下,自从那一回顶破宫口以后,他便不时作恶,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将她弄哭。
一时之间,只听得满室啼哭、兽喘余音不绝。
悍臂将她死死按在胯下,无论她如何哭求,那狰狞蛮横的性器,张脉偾兴的健躯,热烫粗哑的吐息,竟真的如同一头野兽在交颈舔舐、侵犯奸淫着滴粉搓酥的观音。
愈是楚楚可怜,却又愈惹得凶兽想用最残虐的手段将她脐下淫洞捣烂才好。
胯下皮肉相撞,乒乒作响,姜婵被撞得如浪中浮州,头晕目眩,紧紧抱住身前之人,好容易才如盲人遇浮木般拽紧了他,与他一同沉沦在这一方天地。



![《拥有读心术后发现上司是一坨行走的黄色怪物[高h 1v1]》1970版小说全集 之和卿卿完本作品](/d/file/po18/74710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