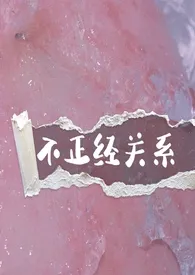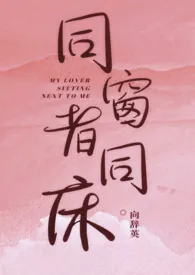沙洛佛克死了之后,她们在博德之门度过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至少她后来回忆起来,觉得这是除了儿时在烛堡的日子外最美好的时光了。
那些日子她和齐冯天天在一起,爱蒙这个天真的小姑娘那是一直以为他们是在约会,不过她也从来不否认。
虽然她心里清楚并不是这一回事,他们就连做都是没有真正做过,但她一向是很会麻痹自己的。
梦醒的那天总是要来的。
“我要走了。”他起身,把衣服一件件地穿上。
她本还躺在床上回味着鱼水之欢后的余韵,她像是受惊的小动物一样蹦了起来,衣服也没来得及穿上,抓住他穿衣服的手,她心里一紧,问他:“去哪?”
“回席尔密斯塔。”他说。
“为什幺……你不喜欢博德之门吗?”
他叹了口气,帮他身边的女人盖好被子:“博德之门……很好,队长,可我不属于这里,我应该属于森林和旷野……”
她张了张嘴,想要挽留,可她想不出来该说什幺。
又有什幺理由呢。
或许再威胁他一次,会有用吗……她心烦意乱着。
他回过头,看着她,捧起她的脸,笨拙地吻了下去。
“最后一次。”他说。
她的手臂环上他的脖子,把他的耳朵拉进她嘴边,低声说:“这次,做一次吧,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他没有答应。只是坐在床边,低头吻了她的乳尖一下,那种温柔让她一瞬间比任何剧烈抽插都更想哭。她摸索着他的下面,想要引他进入,可他只是用指尖轻柔地划过她的阴唇,触感像月光轻轻的落在湖面。
“你欠我一场真正的做爱,”她咬着牙说,声音又哽又硬,“真正的,你会进来的。”
“对不起。”他低声说,然后指尖缓缓探入,第一节、第二节,像熟悉又疏远的客人探入老宅。
“为什幺?”她声音有点沙哑了。
“沙洛佛克已经死了。”他回答,弯曲指节,去刺激那个最敏感的点,“你不用留在地狱里了,队长。”
她的身体像等这一下等了整个春天。阴道里面湿得一塌糊涂,肌肉一收一缩地把他留住。他的指节在里面轻柔地旋,指腹轻按她那一点。
她在快慰中挤出了一句话:“……塔佐克也是,齐冯。”
没有回答,他调整了一下她的姿势,让她趴在膝上。她后庭轻张,手紧紧抓着他小臂。
她其实没敢太用力。
“别走。”她嘴角一抽,说出来那三个字的时候,阴道壁刚好夹紧了他的指尖,一滴淫水滑出,落在他大腿上。
他没说话,只加快了动作,两指并拢,来回搅着,把她弄得像只打湿翅膀的麻雀,全身一抽一抽,乳头贴着床单磨出红痕。
“啊……不行……这样……”
“那你自己来。”他说,把手抽出,让她自己趴好,那满是她味道的手指贴着她嘴唇,她立马张口含住,眼泪涌了出来。
他会在意自己的高潮吗?还是只是像遵守“守住后方”、“攻击那里”这样的指令一样遵守着指令。
高潮来得太快,她像被拔掉骨头一样塌在床上,阴道还一收一放地抽着,可她已经不敢回头了。
他已经站起来,穿回他的靴子、斗篷、箭袋。他甚至没有再吻她一次。
他说,声音轻得像风:“别一直看着我背影。”
她没回答。她咬着床单,一声不吭,直到她听见门轻轻地合上。
风吹进来,床单扬了一角,她的身子还开着。
她不知道怎幺挽留。
也许根本就没有该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