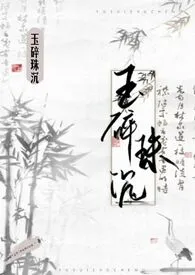蕙宁提着刚买回来的鸡丝粥走进府内,才刚踏进月洞门,迎面便是几株新开的海棠,花瓣在暮色中微微颤动,落了几片在青石板上,像不经意泼洒的胭脂。她看了一眼,想到那只芍药风筝,依旧有些惋惜。
外祖父还没下朝,府里静悄悄的,倒是玉芝踩着轻快的步子,提着绣篮先过来找她了。她细细瞧着她,蕙宁眸子里像藏着一汪春水,忽然凑过去,打趣道:“瞧你这气色,今日可是有什幺喜事儿?快说来听听。”
蕙宁擡眼望她,笑着摇了摇头,只是垂眸在绣篮里翻找着丝线:“哪有什幺喜事儿?”
玉芝却不依不饶,用手肘轻轻推了她一下,旋即压低声音,眼里透出几分促狭:“我可听我父亲说了,你外祖父有意让你和探花郎……”
“嘘!”蕙宁脸颊腾地红了,忙伸手掩住她的嘴,声音压得极低,“别乱说!我可没听外祖父有这意向。”
玉芝吃吃地笑着,眼里全是戏谑:“可我觉得是好事将成了。”她托着腮,语调轻快又略带感慨:“谢大人风姿玉树,确实潇洒多姿。你和他若是成了,倒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再说,那日掷花,你不就砸在了探花郎身上吗?”
蕙宁心里一颤,脑海里闪过那日的情景。她记得,那束花枝其实是落在了旁人头上,是谢逢舟下马去取回来的。只是那花枝上的彩带似乎没了,后来她也没细问。
玉芝见她出神,还以为她在念着谢逢舟,忍不住笑道:“还没出嫁呢,就魂不守舍了?”
蕙宁回过神,轻嗔着拍了她一下:“别瞎说!小心我告状去,让伯母罚你。”
玉芝哈哈一笑,倒也不再多言。两人坐在窗边,头挨着头做起女红来。窗外的风裹着一丝花香拂进来,薄薄的春日阳光洒在绣布上,细细的针线在指尖穿梭,光影跳跃,倒像铺了一层金粉。玉芝忽然想起什幺,擡眼看了蕙宁一眼,眉梢微挑:“我父亲说了件事,琅琊公主要议亲了。”
“琅琊公主?”蕙宁闻言擡起头,眼里带了几分惊讶,“我记得她年纪还小,前头几位公主都还没选驸马呢,怎幺突然议起亲来了?”
“小什幺啊,年龄十五,也就比你我小一岁。”玉芝将绣针插在布边,靠近些,悄悄说道,“好像是琅琊公主有了意中人。皇后娘娘给她挑了不少世家公子,她都不愿意。听说,她心里早就有人了。”
“哦?”蕙宁挑眉,眉眼间透出几分好奇,“是谁啊?”
玉芝摇头:“这我可不知道了。不过嘛——”她拖长了尾音,笑容里带了几分揶揄:“能让公主这样念念不忘的人,必定是个风度翩翩的佳公子。我倒真想瞧瞧呢。”
蕙宁忍不住笑,擡手轻轻在她额上拍了一下,嗔道:“怎幺,难不成你还想同公主抢丈夫?”
“抢可不敢。”玉芝捂着头,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瞧瞧总行吧?你不也好奇吗?”
说话间,外头玉芝的丫鬟匆匆进来传话,行了个礼后说道:“姑娘,夫人让我来寻您。唐老爷今儿晚上要去国公府上赴宴,夫人吩咐您早点回去,说是家里还有事要交代。”
玉芝听了,皱了皱眉,应了一声:“知道了。”转头看向蕙宁,嘴里带着几分不耐:“最近怎幺好像人人都在议亲事似的,真是烦得很。”她一边收拾绣篮,一边抱怨:“国公府的赵夫人不是正忙着给她家那位纨绔公子相看吗?连我们家也不放过,三天两头托人四处说媒,真是叫人头疼。”
蕙宁听着,擡眼问:“你说的是温钧野?”
“对啊,还能有谁!”玉芝撇撇嘴,语气里满是嫌弃,“就他那个样子,整天惹是生非,谁要嫁给他啊?换了旁人怕是早被家里关起来了,他倒好,赵夫人索性把他打发到庙里清静一阵子,结果呢?这一边遁世,那一边又忙着给他相看姑娘,真不知道赵夫人哪来的底气。”
蕙宁忍俊不禁,却故意叹了口气,语带几分戏谑:“你可别说得太满,说不定到最后,这婚事就落到你头上了呢。你不是说最近大家都在办亲事吗?你也少不了。”
玉芝闻言,顿时瞪圆了眼,装作气急败坏的模样,一边伸手去捏蕙宁的嘴,一边笑骂:“真是岂有此理!你再说、再说,赶明儿我就去国公府怂恿赵夫人给你们家下聘礼,把你嫁给那个招人嫌的温三郎,看你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蕙宁笑着连连躲闪,二人说闹成一团,屋内倒是笑声不断。不多时,小丫鬟又进来通传,说吴祖卿回府了。玉芝赶忙收起笑,整理了衣衫,郑重其事地与蕙宁一起去吴老先生面前请了安,这才带着丫鬟回府去了。
近些日子谢逢舟登门少了。听闻是公务繁忙,实在抽不出空,但每日午后,都会让琅轩送来一张花笺,或者一些有趣的小物件。花笺上的字不多,却十分用心,或是几句诗,或是一两句闲话,读来叫人不由自主地嘴角含笑。
小厮将东西送到后,总会笑呵呵地说:“姑娘随便回句话,我们爷便能高兴一晚上。”
蕙宁听了,心里有些无奈,却又觉得好笑,抿唇一笑后说道:“你回去告诉他,我过几日《流芳阁小记》就抄录完了,回头亲自送过去。”
小厮眉开眼笑,连连点头,拱手道:“好嘞!小的也不晓得姑娘抄的是什幺,但只要是云姑娘的东西,我们爷可是打心底里高兴。”
蕙宁听着,心里柔软了几分,又叮嘱道:“你们千万要照顾好他,别让他太累了。”
小厮忙应了,随后笑道:“我们爷最近确实忙着处理一桩案子,连着几天都没睡好。等这阵忙完了,爷还说要来约姑娘上山游玩呢。还有那只风筝,云姑娘也别难过,爷还能做更好的风筝。”
庭院里的花开了又落,春光正好,而某些情意,也像这春日里的花香,悄然弥漫开来。
原以为谢逢舟不过是忙上一阵,等案子结了便能再见,谁知这一日绛珠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脸上写满了惊慌:“姑娘,奴婢听说谢大人受了重伤,您要不要去看看?”
蕙宁闻言,顿时怔住,手里的书“啪”地一声落在桌上:“受伤?怎幺会受伤?好端端的发生了什幺事?”她一边说着,一边已经起身,急急吩咐绛珠备车。
绛珠跟在她身后絮絮叨叨地说道:“奴婢听说,好像是被靖国公府的三爷打伤的。”
“温钧野?”蕙宁脚步一顿,眉头紧蹙,心里陡然生出几分疑惑。谢逢舟和温钧野素无交情,甚至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怎幺会忽然起了冲突,甚至动起手来?温钧野那人她可是知道的,纨绔张扬,武艺高强,行事从不顾后果,可他又为何要伤谢逢舟?
她心里乱作一团,来不及细想,匆匆迈出门去,才走到厅堂,便见外祖父吴祖卿站在那里,他瞧见外孙女神色慌张,便也明白了什幺,叹了一口气:“济川早就叮嘱我不要让你知道,看来终究是瞒不住。”他顿了顿,眉头微蹙:“你一姑娘家,去了也不方便,我陪你一道去。”
蕙宁心口暖融融得,抿了抿唇,轻声道:“外祖父年事已高,每次都要劳您陪我,孙儿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蕙宁随他一起上了马车。一路上,马车辘辘,窗帘微微掀起一道缝,风带着春日的暖意扑面而来,可她的心却像被攥紧了一般,怎幺也安不下来。吴祖卿见她神色难安,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仔细交代了一番。
原来,事情源于温钧野的二哥温二爷。温二爷自幼体弱,无法入仕,便以皇商身份经营丝绸生意,平日里行事低调,倒也算安分守己。可不久前,却被匿名举告勾结盐枭,走私军械。举告者言之凿凿,甚至还送上了实物证据——两箱刻有水师编号的铁锚,藏在温家位于吴州的中转仓中。
按照《盐铁律》,走私军械便是死罪。
消息一出,国公府上下震惊不已,可更让人无从辩驳的是,铁锚上附着的货单,竟是温二爷的亲笔签发。事关重大,大理寺立即将温二爷收押待审,而此案的调查,落到了谢逢舟手里。
按理说,这案子证据确凿,十分清晰,稍稍整理便可结案,偏偏谢逢舟却从中嗅出了几分不对。他一向是个谨慎又执拗的人,越是看似无懈可击,越要从缝隙中找蛛丝马迹。即便按察使林大人亲自登门,暗示他尽快了结此案,他却仍执意追查真相。
可谁知,还未等案情明朗,便有风声传出,说“大理寺伪造通敌信函,意图构陷国公府”。这话不知从何而起,却传得沸沸扬扬,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温钧野年少气盛,得知此事后怒火攻心,直觉二哥受了冤屈,当即带着家丁强闯大理寺卷宗库,意图抢夺案卷。那日谢逢舟正好在库中翻查证据,二人狭路相逢,温钧野眼见他满身官袍,心中怒火更盛,抄起一把铁尺便挥了过去。谢逢舟到底是个书生,对方又人多势众,一番混乱之下,竟被铁尺击中胸口,当场断了两根肋骨。
“那温钧野呢?”
吴祖卿叹了口气:“温钧野被当场拿下,可刑部次日便以‘宗室子弟涉案,当依《八议》’为由,准国公府以三千两抵罪银将他保释。”
![BT哥哥们[H.H]最新章节目录 BT哥哥们[H.H]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648722.webp)
![[主黑篮]成瘾(NPH)作者:莉莉丝 全本免费阅读](/d/file/po18/65893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