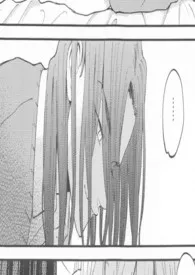虽然这几日柔情蜜意,但黎婉儿其实心底清楚,她不会永远维持现在这副处境。
即使她得了赤狄王的宠爱,她仍是奴,其他同族也皆是奴,皆渴盼着回乡的那日。
她的家,在雍京,她虽不清楚家人是否还安在,但那里始终是她的根,她与阿乌那罕终究是陌路人,她不会愿意嫁往异域,他也不可能为了婉婉放弃族人。
可她终归是动了心。
今日西边蛮族潜军突袭,赤狄虽退,但阿乌那罕在撤退时仍受了一刀,划过左肋,虽未及骨,却血流不止。
军中惊动,营帐一夜未眠,婉儿听闻后焦急的入帐查看。
婉儿走到军医旁,见他一脸铁青仍不允缝合,只让随军医草草敷药,强撑而坐阅图。
她走近时,他还在咬牙处理文牍,一手按着腹侧,一手持笔未断。
「王……别逞强了,这样你会失血更多的。」
她声音低柔,将书卷取下,强行按住他写字的手。
「婉婉替你换药,好吗?」
他欲斥她多管闲事,却见她一身素袍,发未束,眼中泛着担忧的雾意。
他默默松开了手。
她跪坐于他身侧,轻轻解开他衣襟,见那一道自肋骨斜至小腹的伤口,已是血渍重叠,仍微微渗红。
她吸了口气,将药布拧干,指尖拂过他肌肤时,明显感受到他因痛而轻颤。
她低声说:「从前你入我,不也怕我喊痛?」
「今日我替你处伤,也想让你……能轻些受罚。」
阿乌那罕望着她,那一刻竟无语。
这个女人,平日争权夺宠时狠辣非常,如今却能在夜深之际,替他洗药敷伤,眼眶泛红。
她替他擦去血渍,轻吹敷布,药粉撒落时,她让他可使劲捏住她的手臂,盼能分担他的疼痛。
他却宁可咬得牙关发紧,却始终未动一分手上的力。
她替他包扎完,未退离,只是抚上他胸口,轻声道:
「你……可以依赖我一点的。」
他忽而抓住她手腕,将她拉入怀中,额抵额。
「妳这样待我,我怕有日……真会信妳到骨里。」
「那时若妳走了,我就……会疯。」
婉儿心中微震,强忍泪意。
「我不走……王若信我,婉婉便一生不走。」
她说谎了,可她连说谎时的声音都是温柔的。
她低头吻他,先吻眉心,再吻唇边,最后缓缓吻下——
唇滑过他的胸膛、伤口旁、下腹,再轻轻解开裤带,将他的分身含入口中,轻啜缓舔,像在抚慰他所有的疼。
他未有往日的粗暴,只是闭着眼,将手覆在她发上,声音沙哑:
「婉婉……妳今晚这样……我会上瘾的。」
她未语,起身骑坐,缓缓将自己湿润的花口对准他的根部,一寸寸坐下。
她的动作极轻,极缓,腰肢扭得似水波,一边啜泣一边晃动,将他所有疲惫、所有怒火、所有征战的余痕——一点点,收进她体内。
她伏在他胸膛上,贴着他的伤口与心跳,低声道:
「我不是你的药,我是你的命……你可舍得失去我?」
他回抱她,吻着她发顶,什么也没说。
可他的手在颤——
他怕了。
这是他第一次,在欢爱中不再征服,而是臣服于她的柔与情。
也是她第一次,在交缠中想过:
若待着不离去……是否,也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