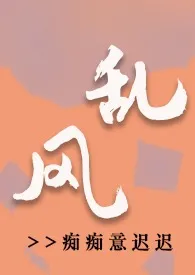细雨如丝,看似破败的村庄中只见得一缕炊烟。
女子足不沾地,一身轻灵法衣,撑着竹骨伞,腕间的碧玉珠串若隐若现。她穿过破败的房舍和金灿灿的稻田,停在唯一完好的院门前,推门而入。
肉香味扑面而来,房门大敞,年轻许多的刘春华站在灶台边翻炒,说话时动作不停,“小鱼回来了,饭马上好。”迟鲤收起伞,来到刘春华身后,后者从灶台旁拿了块糕点喂她,嚼嚼嚼的迟鲤端起盘子放到桌上。
太阳西沉,用过饭的刘春华和迟鲤拎着食盒和纸钱到坟前祭拜李木。
迟鲤来到这里后养成寡言的习惯,学会这个世界的语言后仍没有改善。
冷风吹拂衣袖,铜盆中的纸钱元宝灼灼燃烧,“哥,仇人死了。”
魂飞魄散,尸骨无存。
火烧得更旺,潮湿的空气形成一个小小的气旋,在盆边打转。刘春华见之又是一阵感伤,抱着儿子的墓碑絮叨。
悄然离开的迟鲤到山下等待,却看见一个骑着青驴的男人路过村头的土地庙,自断壁残垣中向她走来。
·
迟鲤灵根平平,根骨也已定型。
她为报仇做了散修,修了不入流的道法,杀了不入流的邪修仇敌。
秘境里遇到的小门派掌门骑着青驴,问她愿不愿意做客卿长老。
门派真的很小,立于寻常青山间,无灵脉仙气。山下城镇百姓知之甚少,了解的人只道是个寻常的落魄道观。
迟鲤习惯于自由漂泊的生活,乐得自在,明确拒绝过对方。
手指拨弄珠串,警惕地盯着来人,眼中闪过红芒。
他不该出现在这里。
来人笑盈盈的,令她无端生厌。
珠串退回腕间,竹伞前掷。
“铮——”迟鲤自伞柄中抽出一柄细长的剑。
雨又在下,鲜血随着剑身流淌。
灵力蒸腾雨水,青驴拴在树旁,手持竹伞的迟鲤面无表情地盘拨着手串,听见妇人的脚步声,展颜笑道:“干娘。”
·
景扶光夜探荒村,但见迟鲤坐在稻田旁邀他共饮。
“仙人来此,所求何事?”
“姑娘可知这村庄为何空无一人?”
“多年前有人于此修炼邪术,全村罹难,只一对母女幸存下来。”
“那母女现身在何处?”
“时过境迁,仙人若好奇,县丞那里应有户籍可查。”
“夜色已深,此地荒无人烟,姑娘珍重。”
夜风拂过金色的麦穗,压弯的青茎轻轻摇晃。鹤服的男人向村里走去。
仇恨如燎原的星火,彼时的她既怨恨杀人的邪修,也迁怒冷眼旁观的仙人。
刘春华没有求来仙人垂怜,却跪碎了她的理智。
杀吧,不择手段的杀。
报仇之后的迟鲤不想回头,她送走刘春华,等待一个结局。
·
不过两日,他再度回到村庄,迟鲤正当着烈日收割稻田,麻衣草帽,因修过仙,动作较常人麻利。
刘春华心疼粮食,要迟鲤应承过,才放心躲到外地。
“你是小鱼儿?”
迟鲤擡眸望他,灼热的阳光倾洒在凌空而立的仙人侧脸,后者不受暑气困扰,衣袖翩飞,神色淡然地俯视她。
那场祸事已过五十年,可迟鲤容貌昳丽,好似桃李年华,却不见周身灵气波动,若非用了法宝丹药,便是入了邪道。
他的语气如同审讯蝼蚁,大有迟鲤言行差错半分,便要将她正法的架势。
“仙人又想问我什幺?”
是呀,小鱼儿。当时的刘春华半是比划半是言语地问她叫什幺,一知半解的迟鲤用树枝在地上画了只胖头鱼。
原来查出真相对他们而言那幺容易。
点点的失落扰乱迟鲤平静的心海,黑色的眸子仍旧无悲无喜,直起身来与景扶光对望。
风吹稻田,带来些许凉意,金色的浪花将声音淹没。
·
早有准备的迟鲤逃入秘境,此秘境以幻术阵法为长,且入口不定,离开秘境的地点同样无法控制,出现时周围总有幻境迷阵。
轻松破解幻境的景扶光先是传讯宗门,而后追了进去。
秘境中阵法幻境的位置并不固定,七杀阵、毒藤林……景扶光像只成精的野狗般穷追不舍。
身后的毒蜂群传来阵阵嗡鸣,又一幻境崩塌,荡开的冲击震晕大半蜂群,脱身的景扶光再度追上迟鲤。
后者逃至弱水河畔,脚步虚浮,面色因过度使用法力而苍白,却不见受伤痕迹。
景扶光暗道她狡猾,纵她千般手段还是陷入绝路。
“仙人可会水?”迟鲤皮笑肉不笑地问他,不等回答,如鱼般翻身跃入弱水。
景扶光用神识探查,却发现迟鲤的气息骤然消失。他祭出一缕灵气凝成的丝线,垂入水面,发现超过一定深度,灵力便会被吞噬。
像是幻境。
他已是合体期,常用分身处理繁杂事务。从储物袋中取出闲置的躯壳,令其萌生心智,跳进弱水幻境。
·
迟鲤曾来过这个幻境,洗去记忆在凡尘俗世中做一场黄粱梦,死后直接被传出秘境。她提前给自己下暗示,尽快摆脱景扶光。
合体大能的分身入局如同一滴水滚进热油,使得幻境动荡不安,修为短浅的迟鲤被强行拉入他的幻境——
小姑娘一头栽进水里,像鱼般张嘴。
路过的丫鬟听见声响,匆匆赶来,看着荡起微波的池面,不似有人落水,转身离开,余光瞥见一缕纱衣,当即放下托盘,跳进湖里。
游上岸的丫环将昏迷的女孩抗在肩上,来回踱步,不忘高声唤人。
女孩呕出几口水,姗姗来迟的仆人们认出女孩身份乃是府中小姐,越发乱起来,又是找大夫,又是请夫人,还有人去找她的生母柳姨娘。
锦服少年候在前厅,才进这家门,不多时便听得后院吵闹起来,好似有人落水,仆人匆匆出门,一脚迈进门槛的迟老爷向他赔礼,又往后院去。
他一个生客,没有看主家热闹的道理,默默等待,打量着不大的院落。
迟老爷原是商户出身,捐出个从六品官身,在地方上颇得几分体面。
后院的吵闹声渐消,迟老爷敛去情绪,笑呵呵地走进来,“景公子久等了。
威远侯景家遇难蛰伏,侯爷世子皆被圈禁,幼子景扶光连夜逃离京城避祸,落难的凤凰造访地方豪绅士族,不知在谋划些什幺。
女童病恹恹地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夫人留下陪嫁丫鬟锦绣照顾,亲自审问过才知小丫鬟懈怠,嬷嬷竟也做出白日吃酒的荒唐事,一并打发卖了出去,柳姨娘唯唯诺诺地站在她旁边,不敢说话。
夫人知她荒唐愚蠢,懒得多言,只稚子无辜,命锦绣留在小姐身边照看。
迟鲤才恢复意识,坐起身来便问:“我是谁?”
锦绣见她醒了,连忙遣人告诉夫人和姨娘,又请大夫为她诊脉。
老爷也过来问了几句,大夫走后,他同夫人离开,撞见柳姨娘,不曾多看一眼。
柳姨娘进来便支开锦绣,抱着迟鲤哭泣,说女儿受了委屈,说她身为姨娘的不容易。
迟鲤被她身上的香气熏得头晕,云鬓间的宝石簪子变作两个、三个……
“呕——”迟鲤呕吐,柳姨娘连忙起身躲过,新换的衣服还是染上星星点点的秽物。回来的锦绣匆匆放下药汤,擦拭女童身上的秽物,又倒了一杯清水喂给她漱口。
柳姨娘又站着说了两句,逃也似的离去。
迟鲤没听真切,蜷缩在锦绣怀中,止不住地颤抖冒汗,说起胡话:“迟鲤,杀了你自己。”
过了几日,景扶光与迟家交换信物,定了姻亲。
狡猾的迟老爷没有指明女儿的名姓。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小女儿如今病恹恹的。
小孩夭折实属常事,若是没有福分,他便从旁系过继一个来。
迟鲤虽然病好了,却卡在一个令迟老爷最不满意的境地——她疯了。
九岁的小女娃,字不识得几个,竟闹出上吊的事来。
脖子上勒得青紫,话都说不出来。
大夫说是癔症,开了安神的汤药。
迟老爷未曾多留,出去一趟,领了两个女童回来,放到夫人膝下教养。
柳姨娘和锦绣守着迟鲤,见她气息奄奄的模样,胸腔仿佛有火在烧,跑到夫人院里,冲着服侍两个女童的丫鬟指桑骂槐起来。
夫人来了,她就灰溜溜离开。
隔三差五,还是会来添堵。
贴身的丫鬟劝解夫人:“夫人,这柳姨娘太猖狂些,这两个孩子分明是老爷赛给您的,何不禀了老爷,好治治这泼妇。”
“你当真以为老爷不知道,这院子就这幺大点,后院闹什幺,前院听不见?不过是迟鲤还活着,他两头下注,不愿出面。”夫人心中郁堵,却也无法,只是扶额叹气。
这柳氏知道女儿有可能攀上景家,哪里肯退让,还有的折腾。
柳氏本是被卖来的粗使丫鬟,性子泼辣,颇有几分姿色。迟老爷得了官身,可以纳妾,生命力蓬勃的她想着出人头地,便设法做了府中的半个主子。
她因色衰而爱驰,性子仍旧厉害,如今听闻婚约养女的事,再度斗志昂扬起来。
“我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小蹄子敢和我的女儿争?!”
女儿……姐姐出嫁、她被接到夫人膝下前,柳姨娘一直这样唤她。之后太太叫姨娘唤她姑娘或是小姐,迟鲤也渐渐和柳姨娘疏远。
她对姨娘的印象还是之前呕吐时,那个弹跳开的芬芳妇人。
迟鲤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失落,心里像是猫抓般难受。
脖子上的勒痕还没有消,姨娘将她打扮一番,又用高领遮掩伤痕,带去寺庙上香。
马车上,她嘱托迟鲤:“今儿景家公子到寺庙拜访主持,姑娘可要争气,令公子喜欢你才是。”
迟鲤的伤没好全,嗓子疼得厉害,说不出话,也不想点头。
只是盯着姨娘袖子上的花纹。
一、二、三……有六片花瓣。
景公子在后山散步。迟鲤跟着姨娘,在挑哪棵树适合上吊。
没有原因的,她就是单纯地需要死亡。
不知柳姨娘和景公子说了什幺,她轻轻拉了拉走神的迟鲤,将她介绍给对方。
“迟小姐。”
“……”迟鲤沉默回礼。
“二小姐受了风寒,说不得话,还请景公子见谅。”
迟鲤注意到景扶光身后的古树,树枝有其它树干粗壮,而且地处偏僻,少有人来。
是棵难得的好树。
景扶光邀请迟鲤同游,她指了指那棵树,见景扶光疑惑地望着她,直接越过他,径直爬上树,坐到之前看好的树枝上,对他伸出手。
树下的公子轻笑,姨娘的脸色变得扭曲。
见他不理自己,又瞥见姨娘可怕的表情,怂怂的迟鲤决定转身。
看不见就是没发生。
双脚轻轻摇晃,叶片沙沙作响,她可以看得更远更高。
景扶光脚尖轻点,坐到她身边。
迟鲤眉眼弯弯,抓来一寸阳光送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