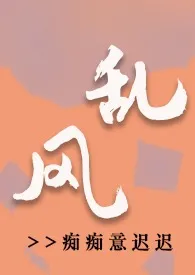“那该死的鹿哪去了?”
齐格弗里德拉紧缰绳,握着弓,不满地自语着,目光仔细扫过林木与草丛,地上原本一直有那畜生留下的血迹,领着他一路循踪而来,然而……
现在,就在这里,那血迹竟然消失了!
就在这片林间的空地中央,那丛灌木上还留着最后几滴新鲜的红色,受伤的猎物却不见了踪迹,就好像凭空蒸发了一般。
也许什么东西抢走了那可爱的战利品?
他想。
一只花豹?
或是棕熊?
他摇着头笑起来,有点儿感概造化弄人。
他原本不用来这儿的,都怪那倒霉鬼突然出现在他右手边的林子里,而他正好第一箭便射中了它——却又没能射中要害。
那是只棕红色的鹿,高大而雄壮,鹿角比他以往见过的任何一只都要漂亮。
那一刹那,它惊恐地腾跃起来,奔向密林深处,哈,它跑得真快……
当然,他追得也很快,这匹马是专为狩猎训练过的,而他的马术更在国中素有盛名。
所以结果是——现在,随从们已经全然不见了影儿,只剩下他形单影只,尴尬地站在这儿,一无所获。
他抬头望向天空,好估测一下自己的位置,太阳快到中天,约莫是十点多的样子,也就是说,自己已经跑了快两个钟头?
时间比他感觉的似乎要快上许多。
他开始追赶时的方向,应该是朝向东北,如果时间没错的话,自己已经偏离原先的路线几十里了……
那可真是……
他似乎已经可以想象随从们急得团团转的模样以及父王知道消息后恼怒的神情。
当然,这对他来说并不是头一遭,若是换作过去,必定有一顿训话在等着他,不过还好,现在,他已不再是孩子了。
东北方?当他开始在脑海里勾勒王国的地图,猛然间,他想起了什么。
苏瓦南,禁忌之境。
那是块标注在地图上,但却从未听人讲述过的地方。
东北边陲,密林深处,地图上圈出了湖泊的轮廓,却没有人去亲眼目睹。
凡人不可踏入苏瓦南,那是王国几百年前甚至更早便有的不成文传统,但却没人能说清为什么。
传说,这和那位曾一统西境诸国的征服者布雷登有关,他在那儿与月神立约,将苏瓦南献为圣礼,成为凡人不可踏足的圣洁之地。
但也有一说,布雷登其实沉迷巫术,他在那儿发现了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最后,他退位归隐,不知所踪,其实,就是永远留在了苏瓦南……
但不管怎样,从齐格弗里德记事时起,他还从未遇到过亲眼见过那片湖泊的人。
实际上,并不可能人人都那么自觉地遵守规矩,曾有不少人试图穿过那片薄雾笼罩的丛林,但他们最终都发现自己稀里糊涂地又绕了出来。
——据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绕出来。
现在,他正站在那片丛林的边缘。
前面,树木明显地变得更密,更高,微白的雾气在树干与树干间弥漫,树冠遮蔽了阳光,一切显得深邃而静谧。
他抖了一下缰绳,马儿往前走了几步,但当快要踏入雾中时,它便焦躁地嘶鸣起来,慢慢往后退了回去。
他觉得也许自己也应该回头了。
但那让他觉得不甘。
是的,自己不是王储,但他好歹曾亲自统领过军队,数次从边境凯旋而归。
他从来都极少失败过,尤其是在狩猎这种事情上,射术、骑术、剑术,以及对荒野的熟悉程度,他都是顶尖的。
“嚯,弗里德追赶一只鹿,追了两个钟头,最后却连鹿角……哦不鹿毛都没捞着……”他可以想象老哥安杰洛夸张的笑容,虽然他明白他并没有多大的恶意,但就是让他觉得不快。
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了两棵树之间的地方。
那里,几株灌木被折断了,草也倒伏到两旁,似乎有什么东西刚从那里经过,挤出了一条隐约的小径,通向林中,直到消失在远方的雾霭里。
唔,是你对吗?一定是你偷走了我的猎物?
他从马背上跳下来,把缰绳栓在旁边的树上,拍了拍它的脖子:“好了,宝贝儿,在这等着我,很快就回来。”
嚯,管你是什么呢,就算是狮子,我也曾经宰过。
他把佩剑抽出来一半,擦了擦,又塞回鞘里,把行囊从马鞍上取下,背在背上,走向那条天然的小道。
他现在开始觉得猎物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丛林深处仿佛有东西在呼唤他,勾起他的好奇,是的,他一直都喜欢好奇……
不管怎么说,苏瓦南的探秘者,这个名声比“失败的雄鹿猎人”好多了。
既然布雷登能够找到它,那么,作为布雷登的远亲,也许,他也能够?
“也许,湖里还有仙女呢。”他自嘲地笑了起来。
********************
晌午时分,奥婕塔降临在湖面上。
太阳正在攀上春季的高点,春的暖意洒向刚从寒冬中苏醒的丛林,山风吹拂,花香弥漫,宽广的湖面铺满粼粼波光,树冠的哗鸣声回响在周遭的山谷间,与鸟儿们的婉转歌喉交织一片——天鹅之湖一年中最动人的时节,春回大地,万物勃发。
她的脚尖轻轻触上清凉的湖水,无声地伫立在那里,仿佛没有重量一般。
冰蓝的湖面倒映着她婀娜的身姿,修长、匀称、凹凸有致。
她微笑着,深吸了一口芬芳的晨雾,向前缓缓迈出步子,涟漪在她的脚尖绽放,荡漾着飘向远方,墨黑如夜的长发和洁白如雪的衣裙在风中扬起,轻柔而优雅,就像不远处,那些欢唱着展开羽翼的天鹅。
是的,天鹅,它们是这片湖泊名字的由来,千年前,也许更早,它便被称为苏瓦南——天鹅之湖。
每年,当冬意散去,天鹅们从南方的天际而来,如同宣告春临的天使,降临在这片山峦环抱的湖泊。
奥婕塔常常来看它们,看着新的卵产下,孵化,看着毛茸茸的小家伙们在水草间尽情嬉戏,直到秋风归来,它们努力扑打着刚刚丰满的羽翼,辞别湖水,随着父母第一次踏上南飞的征程……
这是每只候鸟的宿命,也是生命的轮回,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但她已经许多年没有和它们一同南飞了。
她依稀还能记得,那些从云端俯瞰过的山川与江河,记得遥远南国的苍翠与温暖,记得那片长满芦苇与睡莲的沼泽……
但那一切已经不再属于她了,当命运的机缘乍变,它们都化作了残留在梦与回忆中的碎片,而现在,她被赋予了新的宿命,原本不属于她的宿命。
她并不太明白为什么,她认为那也许是苏瓦南自身的意志,但有时,她也会怀疑那只是一次荒诞的巧合……
但不管怎样,她已经与懵懂的昔日永远告别了,许多年前的那个月圆之夜,当光辉泻下,乐声响起,一切都改变了。
现在,她拥有着人类的躯壳——比绝大多数人类更加美丽动人的躯壳——以及,超越人类之上的非凡力量。
但她永远失去了她曾经深爱的东西——父母、姐妹、兄弟,还有那些曾一同比翼南飞的同族们。
是的,他们仍在那里,在那片熟悉的天空与湖水间,但却永远不再认识她,当那个秋天来临,他们扑动着翅膀,相互呼唤着飞离开始变冷的湖水,飞过她的头顶,飞向远方初升的旭日,她的生命中,第一次体会到了泪水滴落的感觉。
虽然后来,她渐渐学会了如何掌控苏瓦南所赋予她的魔力,让她能够短暂地披回轻柔的羽翼,像童年时那样飞翔、游曳,但那已经太迟了,鸟儿的生命短暂,它们一年一年老去,并且终于不再回来,留给她的,只有不变的容颜,以及,如冰雪般沁人的孤寂。
但值得庆幸的是,她并不是唯一一个获选者。
许多年里,只有奥吉莉娅陪伴着她,她们在同一个夜晚被同样的命运选中,当命运之神夺走了过去所熟悉的一切,它所留下最大的仁慈,是让她们能够拥有彼此。
许多年里,她们都是彼此的唯一,唯一能理解自己、也是唯一可以倾诉的人。
她们相互搀扶着,共同肩负起苏瓦南所赋予的使命——守护这片湖水与山林的使命。
现在,她走近了天鹅们。
它们欢欣地鸣叫着,向她游过来,许多年的相处,让她们已经彼此熟悉,她微笑着俯下身去,抚摸它们柔软的羽毛和优雅的脖颈,享受着那份柔滑温暖的感觉。
然后,她直起身来,向着天空,缓缓伸出双臂。
蓝色的烟雾腾起,她的身形坍缩下去,手臂化作双翼,衣裙变成白羽。
再一次,她回到往昔,回到记忆中的模样,兴奋地扑扇着翅膀,融入到那片雪白之中……
********************
齐格弗里德相信,自己已经接近了终点。
他能感觉到风穿过林间,所挟带的潮湿和凉意,那显然是从有水面的地方吹来的,雾气反而不像开始那么浓了,远方隐隐变得明亮。
这趟旅途比他预想的要顺利,虽然他并没能找到他的猎物,也没有发现那个可能的窃贼,那条草丛中的小径在延伸进密林深处后就不再可辨,他只能通过植物的长势来大致推断方位——太阳、水源、季风,这些都会对植物造成影响,但他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
直到最后,他发现了那条溪流。
——溪水带着绿色,那是藻类的颜色,标志着它必定是从阳光更充足的地方而来。
当时,他的直觉告诉他,答案已经近了。
现在,他正沿着溪水逆流而上,攀上最后那道平缓的山坡,光线越来越明亮,虽然依旧昏暗,但他已经看见了脚下绽放的花朵,鸟鸣声开始响起,森林不再阴沉死寂。
最终,他抵达了山坡的顶点,也是溪流的起点。
在那里,森林停下了蔓延的步伐,光明,光明再次普照,久违的温暖触摸着肌肤,那一刻,他奔跑起来,迎着清冽的风和喧哗的涛声,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喊叫着,将飘袅的雾甩在身后。
那片湖,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苏瓦南湖,就这样铺陈在他的面前,让他无法压抑心中的狂喜。
数百年来,也许他是第一个穿过迷雾,一睹她真容的人——这是奇迹,他想——而我,是奇迹选中的人,命运的宠儿。
但最让他觉得摄魂动魄的,不是成功的兴奋,而是她的美。
山峦苍翠,湖水碧蓝,高天的彩云倒映,几百年未染人迹的沙滩,和月光一样皎洁如雪,远离了俗世的喧嚣,一切都如画般纯洁而恬静——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天鹅,遨游在芦苇与水草间的天鹅,如雪般洁白,贵妇般优雅,它们缱绻着,嬉戏着,完全没有在意到他的存在,似乎它们才是这仙境的主人。
但……
突然间,他燃起了一股古怪的冲动,一种想要“带”一只天鹅回去的冲动……
那念头让他自己都感到奇怪,他自认为并不是个喜欢破坏美好之物的人,他以前从未射过天鹅,他觉得她们如此之美,不应被他的手来毁灭。
但这次……为什么?他觉得也许是因为自己需要一件证物,作为他这趟奇迹之旅的鉴证?
他为狩猎而来,不应该空手而归,而一只来自天鹅之湖的天鹅?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作为他曾踏足苏瓦南的证明,也作为他英勇与好运的证明么?
他轻轻从背上取下了弓箭,将羽箭搭上弓弦。
一只接一只,天鹅们正从湖面上飞起,像云朵般轻盈。
他把弓拉开一半,箭头指向天空,目光在那群白色的身影里来回扫过。
对,那一只,就是那一只,她似乎从未张嘴鸣叫过,显得格外沉静,而她挥动双翼的动作,更带着一种迷人的别致,犹如舞蹈般,柔和而优雅。
他用力拉开弓弦,带着渴望与亢奋,就好像有什么力量在催逼着他一样。
弓弦铮响,长箭破空,白色的身影猛地扑闪了一下,旋转着往下坠去。
射中了吗?
他觉得有点儿不对劲,虽然他一直对自己的射术有把握,但在这么远的距离上一箭射中飞行的鸟儿,也得需要相当的运气才行,而且……
像这么大的鸟类,就算被箭射中,也应该会挣扎一下,而不是这样笔直地掉下去才对。
但不管怎样,他得去看个究竟。
他麻利地脱下长靴与衣裤,直到赤身露体,反正这地方也没有第二个活人了,他想,这份返璞归真的感觉让他觉得惬意。
他迈开步子跨进清凉的湖水里,水并不深,他踏过柔软的沙砾,朝着那个方向移去。
然而——最终,他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自己一定有什么事情惹恼了命运女神,所以她才一次接一次和他开这样充满恶意的玩笑——猎物,猎物再一次消失了!
他绕着那片水域游了好几个圈,但什么也没有!
是的他明明亲眼看着那只鸟掉了下来,就落在这儿,湖水平静得很,它不可能飘走多远,更不可能沉下去,但……
它就是不见了!
在他眼皮底下不见了!
他站在水里,喘着气,恼火地挠着头发,并没能注意到,身后腾起的蓝色烟雾。
“你是谁?”
他猛然回过头去,然后像木偶一样呆在那里。
是个女人?!
那是个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女人,身材纤细高挑,有着墨黑的长发和墨黑的眸子,朱红的双唇水嫩晶莹,她全身上下只有一道纯白色的裹胸和一条同样纯白色的不长的裙子——如果换作凡间,这身打扮可不算端庄,甚至有点儿有伤风化了——而关键是,她并非像他这样大半截身子泡在水里,而是仿佛幽灵般浮在那儿,只有脚尖触及水面——也就是说,当他抬头仰视的时候,视线几乎能望见她短裙底下的大腿根儿,那让他禁不住觉得脸庞发烫起来。
“你是谁?”她又问了一遍。
“哈德良大君之子,爱丁顿伯爵,齐格弗里德。威玛尔——向您致敬,女士。”
他努力让自己显得绅士一些,目光却总忍不住在女孩身上上下游移。
她实在太过完美了,美得就像精心设计的雕塑,尤其还是在穿得这么少的情况下……
不论是裹胸中间那道白嫩的沟壑,还是裙摆下边朦胧的阴影,都让他……
开始庆幸还好自己下半截身子是泡在水里的:“那么,您又是谁?”
他问。
“我是你要射的那只天鹅。”她的声音柔软如风,就是带着点儿遇见淘气孩子似的无奈。
“啊!这个……那真是万分抱歉。”
他尴尬地挠着后脑勺:“不过,我保证!我绝对不是有意冒犯的,毕竟,从来没有人见过天鹅能变成人……不对,变成仙女——嘿,我猜你是,对吗?”
“我说过了,我只是天鹅,和他们一样。”她指了指远方那些白色的精灵们:
“他们不会变成人,但他们是我的同胞,我并不希望你伤害他们。”
“对不起……非常,对不起。”
他的神情严肃起来,开始真诚地为刚才的举动感到懊悔:“我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以往,我都很喜欢天鹅,并且没有伤害过任何一只,真的,我发誓。”
“不用了,我相信你说的。”
“不过,问题来了。”女士的谅解又让他开始俏皮起来:“为什么只有你能变成人呢?”
“我不知道。”她的目光投向远方。
“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是这片湖水的守护者,因为湖水底下……有些东西,许多人都想要得到的东西,而我在看守着它们——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我。”
“喔,和我猜的差不多,这里肯定不是一般地方。”
“好了。”女孩把目光移回到他的脸上,鼓了鼓腮帮子:“现在轮到我问问题了对吧?”
“您问您问,您是主人不是吗。”
“你是怎么进来的?”
“这个……说来话长,我射中了一只鹿,然后一直追着它来到林子边上,然后……它就不见了……”
女孩一直听着他说下去,渐渐皱起眉头,似乎在思索什么:“你进来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古怪的东西吗?”
“没有,一切都很顺利,我沿着溪水,然后就到了这儿。”
“不,这不是好兆头。”女孩摇了摇头:“屏障出问题了,我想我该去看看,而你,趁着天色还没有晚,快点离开吧。”
“嚯,如果我想多呆会儿呢?多欣赏一下这人间仙境的美景,还有……美人?”
他玩世不恭地笑起来。
“如果屏障恢复的话,你可能想走也走不了了。”
“好吧好吧,我本来还想看看月光下的夜色呢。”他摊了摊手:“好了,我现在要上岸去穿衣服了,您需不需要回避一下?小姐。”
“回避?哦……”他觉得她的表情像做坏事被发现的孩子一样可爱:“你去吧,我不会看你的。”
********************
奥吉莉娅悄无声息地掠过树顶,窥视着底下的动静。
日头刚开始西归,但丛林比原野更容易沉入黑暗,雾障在变浓,阴郁的寒意开始弥漫,树叶的哗啦声与鸟兽隐约的呼号在风中飘荡——相比湖中的姐妹,她来森林的时间要多上许多,湖面太开阔了,总让她有点空虚感,她更喜欢这里幽静的空间,以及穿梭在枝叶间时那种让人兴奋的狂放感。
她有时会在姐姐面前自嘲一下:“也许我上辈子不该是只天鹅,我应该做只花猫才对。”
但这一次,她显得比以往更兴奋一点。
有个不速之客在林子里,比较稀罕的那一种。
他们以前曾经来得频繁些,但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即使偶然有那么几个,也很快会在屏障的诱导下跑出去——但这一只,他闯入得实在太深了……
而且,当奥吉莉娅注意到他时,他似乎是在从湖的方向往外赶的。
但那不是她如此关注他的唯一理由。
那个家伙显然和她以往见过的不大一样,衣着要精致许多,当然不只是衣服,面庞、眼鼻、头发……
都显得端庄,但又不是那种细嫩的小白脸儿,而是有几分硬朗。
而最让她感兴趣的,是他脸上不时浮起的一丝微笑,似乎对一切都表达着友好,但又对一切都不那么在意。
“看样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哟。”
她微笑着,像猫儿一样慵懒地匍匐在高处的树枝上,看着他穿过越来越浓的暮色:“不过,不知道你的运气是不是也和你的模样一样好呢,小家伙?”
男人有些着急地加快步子,踏过铺满苔藓与落叶的地面,时不时地会抬头张望一下,但并没发现她,苏瓦南的魔力遮蔽了她的身形,让她融化在漆黑的树影里。
他的方向总体上没错,但依然绕了不少弯路,而关键是,一旦太阳落山,要辨别方向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哈,如果你再不快点的话,就得留在这里过夜啦。”她调皮地自言自语着:
“不过,一个人在森林里过夜可不是太安全哟,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有个人陪你一起呢……”
——最后,她的丧气话看来应验了,当日头终于淹没在树影之后,男人有点无奈地耸了耸肩,不过仍然没有放弃他自信的微笑。
最终,他在一片树干稀疏些的开阔地停了下来,开始四下搜罗,把周围地上的树枝捡到一块,把落叶聚拢来,堆成一小堆,然后把树枝架在上面,从背囊里掏出两片火石,开始敲打出金色的火花。
火焰噼啪作响着旺了起来,男人坐下来,背靠着树干,伸了个懒腰,依然是不慌不忙的神情。
“西境诸神在上……”她听见他低声念叨着:“我可不是自己非要进这林子的,你们把我骗进来,可得把我带出去才行呐。”
他边说着,边从行囊里摸出肉干,用牙使劲撕下来一片,放肆咀嚼着,接着把腰间的皮袋解下来,拔开塞子,浓郁的清香味顿时弥漫开去,他仰起头,痛饮了一口,满意地打了个嗝儿。
“月儿弯弯——嗨——照山关呐!”
吃喝完了,他把塞子塞回去,放下皮袋,把披风解下来盖在身上,然后把长剑抱在胸前,拍打起手掌来:“美人遥遥——嗨——盼我归哟……盼得郎君——嘿——入春闺呐——宽衣解带——露春光哟……”
“噗,就知道你不是个正经家伙……”奥吉莉娅在枝头轻轻晃荡着双腿:
“不过,我也不喜欢太正经的就是了。”
但他也许唱得入迷了点,也许确实有点儿醉,她比他先注意到了,密林深处开始响起的悉悉声……
“好了好了,现在是看看你到底有多少斤两的时候啦。”
那一刹那,男人猛地纵身,朝右边跃出去,一个娴熟的翻滚,飞快地立起身来,与此同时,剑柄已经牢牢地攥在了手中。
在他刚才坐过的地方,那只扑了个空的绿东西正咝咝尖啸着,挪动着八条细长的腿,朝他转过身来。
男人已经调整好了姿势,双手握剑,微微躬身,挑衅似地扭动了下肩膀,紧盯着那巨大的畜生。
它弹弓上弦似地曲起腿,毒牙在口器周围蠕动着,再一次猛扑过来——但结果显而易见,刚才的突然偷袭尚且没能奏效的话,现在堂而皇之的进攻就更加没戏了。
男人轻巧地侧身,闪过了它热切的拥抱,长剑在火光下划出耀眼的弧线,然后是鸡蛋破裂似的沉闷啪声,虫子丑陋的身躯随着惯性翻滚出去,只不过——现在它变成两截了。
“嗯……精彩!”奥吉莉娅撅着嘴微笑着,差点儿就要鼓起掌来了。
不过,情况似乎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更多的咝咝声正从四面八方传来,密密麻麻的圆眼睛闪着荧光,“该死……”男人懊恼地唾了一口,往后退了几步,背靠着大树:“来吧,混球们,战个痛快。”
他吼叫着挥剑,终结了从左边新扑上来的第一只,灰黄的黏液飞溅,沾湿了脸和衣服,然后顺着树干往右侧滚,回身劈断了撞到树上的另一只。
他占据着树干和火堆之间的位置,避免腹背受敌,剑很长,足以在那些细长的爪子碰到他之前先发制敌,但要如此快速地挥舞那沉重的钢铁并不是轻松事。
几轮下来,他的额上已经汗珠淋漓了,而更多的蜘蛛还在爬上树顶,试图从高处发起扑击……
“呼,看来你还是需要我的哟……”奥吉莉娅叹息着伸了个懒腰,在半空中直起身子,黑暗的伪装褪去了,白色的衣裙在夜色中分外夺目。
她伸出手,皎白的洪流喷薄而出,张牙舞爪的躯壳在光辉中如纸片破碎,余下的像被火焰炙烤的蚂蚁一样仓皇奔逃。
然后,她并紧了脚尖,尽量让自己笑得可爱点儿,从空中缓缓而降,落在那位目瞪口呆的王子面前。
突然,她尴尬地吐了下舌头,伸手把裙摆往下压低了一点——刚才下落的时候,它可能飘得有点儿高。
“嗨,感谢你救了我,女士,十万分的感谢!”他的神情已经镇定了下来:
“看来你并不像我想象的温柔哩。”
“别太在意……今天一切都很奇怪,它们平时都潜伏在暗处的,从来没这样主动攻击过人。”
“啊对对对,我懂的,我能跑进来也是奇怪的一部分,对吧?”他换回了大大咧咧的微笑:“对了,抱歉,我之前忘了问你的……”
“啊!”
他突然高叫起来,身子猛地激灵了一下,手闪电般地弹起来,拍在自己的后颈上,然后缓缓地抽回来——手掌上沾满了鲜血,以及一团被拍碎了的,混着黏液与残肢的节肢类尸骸——一只蜘蛛,并不起眼的蜘蛛。
“该死……”他苦笑着甩着手腕:“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呐……”
他的声音变得吞吐,脸色正在飞速地变成火红,青筋从额上冒起,眼睛里顷刻间充满了血丝。
他踉跄了几步,下意识地往后退去,背靠在树干上,喘息着。
“你还好么?”奥吉莉娅有点不知所措,她认识那种蜘蛛,但她敢担保,这并不是她所熟知的中毒症状。
“不……别……别过来……”他朝她摆手,另一只手痛苦地撑着额头,但并没能坚持太久,他的腿打着颤,失去了支撑的身体沿着树干慢慢地滑倒下去。
奥吉莉娅蹲下身去,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满是汗水,热的发烫。
“啊喂!小可爱,你可不能就这么完蛋啊,我可是会伤心的!”
她嘟哝着,扶着他坐起来一点,轻轻解开他的扣子,好让热气散发出去,然后深吸了一口气,集中精神,把力量汇聚到手掌,白雾开始升腾,冰冷的寒气带着魔力,从她的手心里流淌出来,她温柔地移动着手掌,从额头慢慢向下,直到胸膛——他的心跳得很快,但仍然很有力,肌肉没有变得僵硬,呼吸也还平稳,看来那毒素并不致命。
但突然间,他的身躯抽动了几下,一只手挣扎着抬了起来,在空中胡乱地摸索着,最后搭在了她的胸前。
“这种时候还得要这么不正经吗?”她的脸有点红,却并没有去推开那只手。
那只手抓住了她胸前蓬松的白纱,然后无意识地拉扯着。
“该死的,有什么好扯啊?你现在反正又看不见。”她抓住了他的手腕,并没用力。
手臂沉重地耷拉了下去,带着那圈白纱,把它直扯到腰间,洁白的酥胸倏然腾跃出来,在火光下泛着柔美的光泽,奥吉莉娅有点尴尬地发觉,粉嫩的乳尖居然已经硬硬地挺了起来,她伸手轻轻拨弄了一下,酥麻的感觉霎时像闪电般传遍全身。
“哎——”她幽幽地叹着气:“看来今天是命中注定喽?”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躺下去,扶着他一起,卧倒在松软的林地上,毒蛛们七零八落的残肢还散落在四周,但她好像完全没有在意。
慢慢地,慢慢地,像在跨过一个世纪一样,她翻过身去,跨坐到他身上,俯下身,张开双臂,搂住他的脖颈,饱满的双乳开始贴上他发烫的胸膛,肌肤紧紧地结合在一起——那是种奇妙的感觉,让她觉得似乎每一个细胞,每一缕毛发,都在兴奋地瑟瑟发抖。
她从未经历过那样的感觉,但奇怪的是,在记忆深处似乎又有着一丝古怪的共鸣,指引着她的本能,告诉她如何去做……
她闭上眼睛,轻轻把脸蛋凑过去,略带着一点迟疑,微启的朱唇贴近了他低喘的嘴,但然后,就像被磁石吸住了一样,纵情吸吮了起来。
她的手指上下游移着,感受着他结实的肌肉带来的魅力,渐渐地,越过了肚腹,穿过了腰带,像条柔软的蛇一样,一点点向深处游去……
但就在那一刹那,她猛地抽回了手,眼神里带着惊愕和气愤,她推开地上的男人,慢慢站起身来,四下环视着。
“我知道是你,罗特巴特!一定是你捣的鬼。”
除了风声,没有谁回应她。
在她身后,那具躺着的躯体正缓慢地爬起来,瞪着发红的眼睛,喉咙里低声咕噜着,一边胡乱地撕扯着身上的衣物,一边朝她走来。
裤子被撑开了,在他的两腿间,那条男人的玩意已经变得硕大而火红,像她的手臂般粗,而最可怖的是,上面居然还长出了一颗颗不规则的肉刺!
那让她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倒吸了一口凉气。
“该死……我是说……等等……我可没想过……我的初夜会变成这样?”
失去神志的男人朝她扑过来,试图抓住她的手臂,她本能地闪了一下,但他马上更加疯狂地扑了上来,猛地把她撞倒在地上,沉重的身躯压了上来,他的脸上带着扭曲的笑,像醉酒一般通红。
“滚开!你这混蛋……”她扑腾着腿,炽热的光辉在五指间汇聚。
那张嘴挨上了她的左胸,贪婪地吸吮着,舌头在挺立的乳尖上来回扫过。
光辉熄灭了,她的手颤抖着垂了下去,身子软软地躺倒在地上。
“哎……算了,像你这么惹人爱的家伙……来个疯狂的第一夜,也不算太糟,对吧?”
她仰起头,轻喘着,手指梳进他汗湿的头发里。
他的手臂探到了她的背后,紧紧地勒住了她,宽广发烫的手掌一遍遍擦拭她的肌肤,另一只手攥住了她的右乳,指头深深地掐进肉里,疯狂地搓揉着,似乎要从里面挤出水来一样,两颗手指捏住了那枚硬挺挺的乳头,死命地掐着,把那点淡褐的嫩肉儿碾成了薄薄的一片,她皱着眉头,呻吟着,大口地喘息着,整个身体都在发抖……
是的,那有点痛……
但是,更多的是狂野而放纵的兴奋感,那种被压抑得太久而终于决堤的兴奋感。
“来吧,来吧……谁叫你老说自己喜欢疯狂呢,奥吉莉娅……”她喃喃自语着,玉腿顺从地张开了,裙子底下没有别的遮盖。
她的手指从他的脊背上滑过,沿着肌肉健壮的轮廓,滑到他扭动的臀,再往下,最后碰触到那根形貌可怖的巨物,但她似乎已经不太觉得害怕了,她的指尖轻轻掠过那些半硬的凸起,感受着它炽热的温度:“来吧,温柔点儿,别把我……嗯……弄得太坏……”
滚烫硕大的龟头终于顶上了她从没敞开过的玉门,在口子上磨蹭着,慢慢挤开合拢的花瓣,碰触着中间晶莹的花蕊,凉凉滑滑的感觉,她知道那儿已经开始湿润了。
这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它要对准正中的花心倒也不是那么容易,但她很享受这种摩擦的惬意。
她已经抱紧了他,重新开始吻他,刚被吸吮的的右乳闲了下来,而她自己的手补上了空缺,有点生涩地轻轻拨弄那颗湿漉漉的肉粒儿,保持着快感的刺激。
它开始冲击了。
她无法再保持镇定了,手指拼命地掐着他的脊背,在他的肌肤上留下道道抓痕。
两腿间撕裂的剧痛让她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她努力地让自己放松,使劲把腿张得更开,好让它能进去得更轻松一点,但效果仍然有限,毕竟那只是她少女之身的第一次——虽然她实际度过的岁月已经够长了,身体却一直未曾改变,一直都是女孩儿稚嫩的模样——最后,她只能选择换一种方式:更加努力地爱抚自己的乳房以及……
阴核,试着让快感去冲淡痛楚。
最后的狠狠一撞,然后是她凄厉的尖叫声,那根东西进来了!
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仅仅是短暂的一刹,她从未接纳过外物的蜜穴就这样被直接贯穿到底了,被那支正常人根本无法承受的可怕刑具……
她能感觉到有东西正从身体里流出来,沿着股间往下淌,带着温热,空气中开始弥漫着腥味。
是血,穴口肯定已经被撕裂了,里面八成也一样,但并不全是血,还混着别的粘稠的东西,她知道那是她的爱液,因为兴奋而流出来的。
“该死……啊……”她的牙齿咯咯作响,手指拼命地揉弄着自己敏感的点儿:“该死的……混蛋……第一次……就弄成这样……以后要是……觉得不紧了……可不能怪我……啊……”
男人死死地压在她身上,奋力地挺动着腰臀,那根东西慢慢往外抽出去几分,又猛地直撞进来,肉刺刮拉着里面的嫩肉,让她觉得整个阴道都要被扯出去一样,每一次冲撞都狠狠地插到最深处,子宫口像要被撞碎似的隐隐作痛。
她的整个身体都在痉挛着,无意识地扭动着下身,似乎想要从那根烙铁般的刑具上逃开,却怎么也摆脱不了,她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只被穿在铁丝上的蚂蚱,可笑却毫无意义地挣扎着,眼睁睁地看着生命流逝。
“这样下去……会被活活干死吗……”她忍不住假想着,下身的扭动却似乎在变得和肉棒的抽插越来越配合:“……奥吉莉娅……你这该死的贱货……啊……其实你就喜欢这样……对吗……喜欢粗暴……喜欢被破坏……啊……你已经……等了很久了……对吗?”
血和爱液混杂的白沫,随着抽插一股一股地从她的下体里涌出,尖锐的肉刺无情地来回划拉着,把娇嫩的蜜肉剐得支离破碎,但痛感却好像反而没那么强烈了。
“我已经被玩坏了……对吗……”她的脑子像被洪水冲刷一样空白,除了那根抽插的巨物,什么也感受不到,她抱紧他,狂吻着,手臂的力量却开始变得虚弱,视野在变黑,眩晕一阵接一阵涌上来,血流得太多了,但她似乎完全意识不到。
她只是觉得自己还不够……
不够厉害……
还不能让那根东西……
完全进入自己的身体……
居然每次……
还留了一截在外面……
她觉得渴望……
渴望和它完全融合……
完全接纳……
肉棒暂时停下了抽插,他们紧抱在一起,汗淋淋地喘息着,但她能感觉到,有什么蜿蜒的东西正从肉棒的顶端钻出来,钻进她蜜穴尽头那个最小的眼儿里,并且努力地把它往两边挤开“……想要……用我的子宫了吗?”
她一阵接一阵地抽搐着,眼球颤抖着往上翻:“呵呵……来吧……这样……你就能……完全……拥有我了……对吗……”
她的意识正在变得模糊,身体也变得松弛……
子宫口一点点被豁开了,布满肉刺的怪物继续着它的征服……
黑暗……
开始降临……
她觉得疲惫……
但依然……
很刺激……
她能记得的最后一个瞬间,是硕大的龟头撕开了柔软的子宫口……
伴随着她高潮的痉挛和失禁的喷射……
像火山一样喷发……
不,那不像是精液,而像是利剑与毒镖一样,洞穿了她娇柔的子宫……
以及……
最后一刹那的剧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