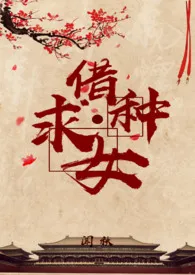男人推开门走进屋子的时候,房间里一片明亮。
门厅的沙发上叠着大红色盒子。
最上面的那个盒子已经被拆开了,一条崭新的红内裤躺在最上面。
他走过去低头看了看,认出了这是一条男式的内裤。
大红色的盒子设计有些俗气,上面还印着“伊爱斯”“吉祥如意”——男人微微皱了眉头。
虽然这内裤目测质量还行,但是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牌子,大概率是地摊货了。
地摊货,他从小锦衣玉食——妈咪和父亲从来不曾在经济上亏待过他——他原则上是不穿的。
何况还是大红色的。
不会是连月给他的吧?
男人低头看着这红彤彤的内裤,有些人,说起来月薪是有两万——已经超过95%的人群了,其实常年花钱大手大脚的,经常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他倒是知道的。
估计也是送不了什么值钱的礼物。
一整晚都在卧室,也没能下去见“那几位客”,男人心里又是一松。把视线从这盒子上挪开,他在走向卧室的时候,瞄见了书房里的那个人影。
女人穿着粉色的睡衣,正在他的书桌前拿着毛笔在细描着什么,神色专注。
他原本放在桌上的笔记本和文件被她推到了一旁,笔记本后背盖上面的火星人标志还在一闪一闪的散着蓝光。
没有急着进去,他反而在门口站住了看她。
一颦秀眉如月,微微挺立的鼻子,微嘟的唇。
睡衣空荡荡的在她身上挂着,锁骨瘦削完美——惹人忍不住想要伸手去握。
她垂眸细瞄,一举一动都自有宁静的气度散发了出来。
女人低头写了一会儿,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抬头一看,对他嫣然一笑。
“怎么起床了?”
男人也笑了起来,走过去低头看她写的字。一阵淡淡的香水味道传了过来,弥绕在笔尖,似有似无。
女人含笑不答。
“林花谢了春红——”
他站在她身旁,低头念诗。宣纸上的这些字大大小小,歪歪扭扭,论笔力却是不大过关的,只是能认清罢了,“今天怎么这么有雅兴?”
“季总我这几个字写的怎么样?”
女人却似对自己的写字水平毫无所觉,只提着小楷狼毫抬头看他笑。灯光打在她脸上,肤白貌美,美艳非常。
四周装潢时尚——红袖添香,美宅美人。
男人站在旁边,却只是低头看着这字,笑了起来,没有说话。
“季总品鉴品鉴我这字?”
女人却不依了起来。她笑嘻嘻的样子,右手依然提着毫笔,左手却故意伸了过去挠他的衬衫衣扣。
男人微笑着一动不动,任由她的手指落在了身上。
扣子被人轻轻拨动,带动衣料微微触碰着皮肤,就连身上似乎都痒了起来。
“好诗。”他最后说,又一把握住了她的手。
“季总人家让你品鉴字,没让你品鉴诗——”女人笑了起来,故意娇声说话,被人握住的左手还在轻轻的挠。
“好诗。”
男人又笑着说了一次。没忍住把这只作乱的小手拉起来亲了亲,男人又伸手去握她那只提着狼毫的手,声音低沉,“字嘛——”
他笑了起来,“要不我来教你写就好了。”
“好呀。”
女人扶着桌子站了起来。却不知道扯到哪根筋,又微微皱眉嘶了一声。
“怎么了?”身后有声音问,“要不还是去躺着?”
“我不。”男人已经坐下了,女人又往他身上一坐,“难得今晚季总有雅兴——”
“我多的是雅兴。”男人轻轻揽住了怀里的软玉轻笑。
初三的机场灯光闪动,一架飞机刚刚离地起飞。
黑色的汽车停在了疗养院的楼下,层层守卫的二楼病房里有人睁着眼睛无聊的看着天花板,门却突然被人推开了。
他扭头看去,眼睛亮了起来。
“大哥。”他喊。
“身体怎么样了?”来人走到床边微微含笑,神色平静。男人黑大衣遮挡的手腕上,却只有一块陈旧的手表——
一如以往。
市中心某个大宅的二楼卧室书房里,穿着睡衣的女人坐在了男人的腿上。男人神色沉稳,手握着她的手,慢慢提起了笔。
墨尖一下,一顿,白色的宣纸上一团墨色——又是一挥,回笔。一条横线跃然纸上。
笔走游龙。
“哎呀——”女人低头看字,一片心喜的赞叹。
“连月我可不穿红色的内裤。”男人的声音突然在她身后响起,声音低低,“就算你拿零花钱买的,我也不穿——你下次要买黑色的。”
顿了顿,他又补充,“白色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