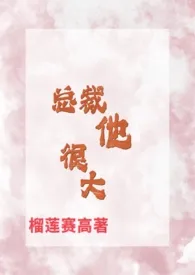正当杜竹宜忐忑之际,她被拦腰抱起,后背紧贴父亲胸膛,两个膝窝一左一右分开,被握在父亲手中,腿心完全露出,仿佛幼儿被端着——把尿!
把尿?
父亲,要就着这种把尿的姿势,从后面c进来?!
可杜如晦只是这样端抱女儿,走到一丛h色木槿花前,轻轻巧巧地对女儿说:“心肝儿,你许久没溺尿了,趁四下无人,撒泡尿在这里,给这山谷浇浇花,以表纪念罢。”
饶是杜竹宜刚刚才突破一道心理防线,觉得主动向父亲求欢不再是件难事,但,被抱在父亲怀里,被父亲盯视着,在野外撒尿,还是太超过了!
毕竟她是十五岁!不是五岁!
“不不不,不可不可,这个决不可!”杜竹宜头摇得飞快,身子也开始挣扎,整个人都在认真向父亲传达她的抗拒。
杜如晦把住女儿两个膝窝,将她牢牢钳在怀中,装作对女儿为何抗拒十分不解,“为何不可?为父又不是没为心肝儿把过尿。”
“咦?”杜竹宜奇道,“我怎不知?”
杜如晦笑道:“心肝儿那时才一岁不到,你不记得也不足为奇。”
“哎,宜儿小时候的事,怎好拿来与现下里相提并论!况且,况且宜儿从未在户外溺尿过,无论父亲如何说,宜儿都绝不会在此溺尿的!”差点被父亲带偏,杜竹宜再度坚决拒绝。
“从未在户外溺尿,那岂不是心肝儿的头一回?今次,心肝儿便把这头一回,给了为父如何?”
杜竹宜快晕过去了,父亲,这是在对她撒娇么?而且,把自己的头一回给他,这话,听着怎的这般暧昧狎昵?
杜如晦见女儿不语,并不以为意,仍极力劝勉道:“心肝儿,此地再无旁人,为父又决无理由对第三人提起,心肝儿你在此撒尿浇花的事,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况且,心肝儿不是饮过酒,所谓酒壮人胆,一泡尿不过呼吸之间,心肝儿闭着眼,听个声儿,就结束了。快,尿罢。”
说完,他嘴里吹口哨,发出“嘘嘘——”的声音。
父亲他?竟然嘘嘘!
若非被父亲悬空抱在怀中,杜竹宜敢肯定,她此刻已经摇摇欲坠。
“怎会是只有父亲与宜儿,这山谷中还有数不尽的鸟儿蝶儿呢。”她勉强打起精神,还想与父亲讲讲道理。
似是为了应证她的话一般,一只翠色的蝴蝶,扑扇着翅膀,停落在她鞋面上,也不怕人,与她翠色竹叶纹的鞋子融为一T,仿若原本上面就有这样一个蝴蝶结!
杜竹宜惊愕了一瞬,面上腾地一下红如滴血,以袖遮面,羞道:“父亲,您看嘛!”
杜如晦见状,笑从颊边生,自得道:“蝴蝶偶然寻香而来,不啻有意,必是也欲心肝儿为它浇花。心肝儿,你注意听那泉水流淌声,为父再助你一助,不会很难的。”说完,他便不再说话,一径“嘘嘘嘘”地吹起口哨来。
先时父亲一直同她说话,杜竹宜一直很紧张,又要想词反驳他,倒不觉得甚么。
此时他不再言语,不远处——涓涓石上水,湍湍落深潭——的种种流水声,便听得分明,和着父亲的口哨声,脑子里一根绷紧的弦,变得越来越细,中间有断口迅速向两边分开……
飞泉既相导,口哨频相催——
阀门大松,有热流溶溶泄泄,滴落在花叶,倾泻于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