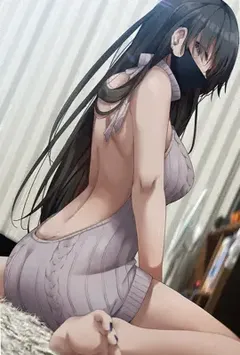一阵敲门声将昏睡中的杜竹宜吵醒,朦胧中,她听到父亲与杜常说话的声音。
“老爷,门房来报,蒋谓蒋老爷来访。”
“好,我去迎一下,你守在门口,别让人进来。”
“是。”
一阵悉悉簌簌的声音后,杜竹宜知道父亲暂时离开了书房,直至这时她才感到神魂归位,扑扇着眼睫,睁开眼睛。
发现她正躺在父亲书桌后,由深蓝色帷幕隔开的里间的罗汉塌上,此时帷幕合拢,仍在微微抖动,想见是父亲离开前为她拉拢的。
她坐起身,“呀”,她讶异地轻呼一声,原来她的衣裳仍是散开,此刻盖在身上的锦被掉落腰间,一对丰硕雪白的大奶子暴露在空气中,她脸一红,抿了抿唇,裹着锦被,趿着鞋,起身时差点一个趄趔,蹙着眉,夹着腿朝外间走去……
少顷,杜如晦引着蒋谓,回到书房。“蒋兄,请坐。”
他一面招呼蒋谓,一面不动声色地分开帷幕,往里看了看,发现在塌上睡着的人儿不见了,飞快地四周打量一圈,不见踪影,他心道,难道是回后院去了?
“怎么了,可是有甚么不对?”蒋谓在他身后问道。
“没甚么。”尽管心中狐疑,杜如晦仍是坐回书桌后圈椅中,这一坐下,便发现了异状。
趁着杜常给蒋谓上茶的功夫,杜如晦往后退了退,果然在书桌下看到了女儿的身影。
这张书桌两边有柜,前方有挡板,底下有踏板,女儿围着锦被蜷缩其中,正忽闪着水润大眼睛望着他,乖巧又俏皮,如她自己所说的,像个小N娃——裹着襁褓躺在摇床中,刚睡醒便要找父亲…
杜如晦直觉自己一颗心变得无b柔软,他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儿,恰似最出色的庄稼人能将土地锄得松软般,令他的心地松软而有活力,生长出对她的无限爱意,看着她便觉得可爱,看着她便觉得心疼!
杜常这时退出去了,蒋谓看杜如晦低头不语,便问道:“杜兄,我可是来得不是时候,看你像有心事?”
“没有的事,蒋兄无论何时来,杜某都倒屣相迎。”
“哈哈,”蒋谓笑得见眉不见眼,举起手中的茶盏说道,“话是这么说,坐着这小鼓凳,喝着这小盏茶,杜兄你这待客之道,可不像多欢迎。”
杜如晦神色自若地说道:“蒋兄又不与别同,我们尽可换个地方,推杯换盏,无所不谈。”
蒋谓连连摆手,说是来告诉他,新来的知州上任三把火,据说是要从盐业开始烧起。
这事杜如晦也收到风,就说已经有了些应对计策,到时真要有事,再请他帮忙。
二人又从建康城的官场到商场的聊了几句,见蒋谓既不说有事,也不说要走,杜如晦桌子底下还藏着他的美娇娃,不免心中着急,便直言道:“蒋兄若是有甚么难言之隐,不妨直说,看杜某能否为你参详一二。”
蒋谓看了看杜如晦,面露难色地道:“确实有一事令我牵肠挂肚,想听听杜兄的意见。”
杜如晦做了个请的手势,说道:“蒋兄尽管说,我定知无不言。”
蒋谓这才犹豫着说道:“其实是因我儿方胜的终身大事,杜兄可还记得,两个月前,我与方胜去到扬州,多蒙你款待,还闹出了乌龙,连累杜兄你中了春药……”说到这,他拱手施了一礼,以表歉意。
杜如晦摆摆手,示意他不必介怀,这事早已与蒋家父子说开了,况且,当时发生的事,可说是他这一生最美丽的意外,深心里,他感激他们还来不及,只是这事不能与人言说。
杜如晦正待说些甚么,突然面色一变,在空中挥着的手霍地扶在桌边,双脚用力蹬在地面,僵直上身,才忍住没一跃而起——
一双柔若无骨的小手解开他的K带,扒拉出他沉睡中的阳具,接着,那软趴趴的一根,便进入了一个温暖湿润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