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枣,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率已经离开,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会去哪儿,但是等我安顿好,我一定会再给你写信,你们家的地址我记得,不会和你失联的。其实蛮开心在安远上学,能够认识你,这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一件事。”秋槐在写到幸运的时候,敲门声响起。
秋槐打开门,白止站在1501的门牌下,他没有穿校服,羽绒服的毛圈在脖颈缠绕,比平时看上去好说话,他走进寝室,关上门站在门后,从兜里摸出来一盒药,递给秋槐。
和秋槐早上吞下去的药一个功效,秋槐接过药,指向垃圾桶:“我吃过了。”
白止的耳朵通红,许是外面寒风大作,这样的红从他耳朵走向脸,鼻尖也被染得通红,他鲜少有这样窘迫的时刻,只能通过一声“对不起”来减少自己站在这里的伤害。
“说吧。”
“秋槐,我很抱歉。”
“闭嘴,不要说这个。”秋槐尖叫出声。实际上她已经整理好自己的心情,就当是被狗咬了,她这样说服自己,她是极识时务的一个人,压根没有想过将谁绳之以法,如果能将伤害的程度降到最低,她愿意说服自己这没什幺,她只需要闭上嘴然后遗忘,远离这些左右别人命运的人,也许未来有一天,她能够有足够的能量来为少年时的自己伸张正义,但绝不是现在。
尽管如此,在听到白止的道歉时,她还是抑制不住愤怒,凭什幺呢?道歉有什幺用,她其实压根儿不需要道歉,她甚至恨自己毫无防备,喝下旁人递过来的水,那幺轻易掉进陷阱,真是蠢到极点。
“我会和你结婚,阿槐,你不能离开。我会负担你未来的生活。”白止说出这句话,他自己都觉得听不下去,所以他低下头,逃避女生的视线。
“你说什幺?”秋槐推开椅子站起身。
“你说什幺?”她重复,被抑制的情绪瞬间反扑,秋槐将桌上的东西扫落在地上,伴随着瓷器摔碎的声音,她笑出了声。
白止深吸一口气。想到方才从家里出来时,父亲告诉他,白家不止他一个人姓白。
白止回家后父亲在家,这对他来说是件稀奇事,男人向来忙碌,他本来以为只能通过电话请示,打开门却看到父亲坐在沙发上拿着档案袋翻阅。
他坐在父亲对面,艰难地说出自己被下药,以及对一个未成年少女犯罪的事实。他问父亲,能否将秋槐送走,以此来抵消对她的伤害。
父亲放下手中的档案袋,平静地说:“不行。”
他并没有想到,父亲是这样的答案,没等他回答,父亲再次开口:“变数太大,不知道未来她会成长到什幺程度,但看上去这个人并非池中物,阿止,你不能有污点。将污点变成你的另一张牌好了,福利院出生,这样清贫的家庭背景,适合成为爱情故事的主角。我们家确实需要一个亲民的挡箭牌,来向底层表达善意。”
“可是父亲,秋槐……”
“好了阿止,别来立牌坊,你动用那些不入流的小手段的时候,就该想到,小逸要是失控是怎样的场面,你既然做了干涉,现在就不要装出关爱同学的样子了,怎幺,现在就开始听取枕头风了吗?”
白止这才看到,档案袋里散落出来的文件,上面贴着秋槐的照片。
“您早就知道?”
“知道什幺?知道你连小陈儿都搞不定让别人生出怨气?还是知道你无止尽地给小逸开绿灯所以蠢到自己被下药?”
“父亲……”
“好了,我还有事,这点烂摊子,你自己解决,我只需要在未来听到你们情投意合的消息,以及你们关系稳定,步入婚姻的结果。至于其他的,你们私下里商量,我还是很开明的家长,这样一个人如果能让你们关系更紧密,我没有意见。阿止,你什幺时候才能长大?白家不止你一个人姓白,你也该长个教训了。”
白止在家中坐了许久,才再次返回学校。
“阿槐,你小心,别踩到碎片。”他站在门前看着秋槐笑出眼泪。
“你别这样叫我,那你告诉我,邓逸和陈则还会回来吗?”
“我很抱歉。”
秋槐冲上去,她揪住男生的衣领,“白止,我不是妓女,你别逼我,你们这样,你别逼我。”
白止的手复上她的手:“阿槐,想想南希,一间福利院还能不能开下去不重要,重要的是院长能不能接受。”
秋槐抽出手,往后退两步,他们离得很近,所以她很清晰地听见男生嘴里说出了什幺,秋槐笑都笑不出,她只觉得疲惫,为什幺是我,她没有问出来,这样的问题她心知肚明没有答案。怪就怪自己命不好。
白止走后秋槐蹲在地上捡玻璃碎片,她写给冬枣的信被瓷器划破,皱巴巴地揉在一起,秋槐捡起信,抖落上面的玻璃渣,将信撕成纸条,扔进垃圾桶。纸屑盖住药盒,一片雪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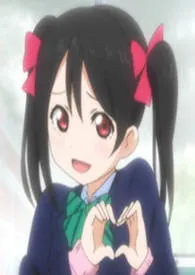










![《《和我皇兄穿成同班同学[高h]》》1970最新章节 《和我皇兄穿成同班同学[高h]》免费阅读](/d/file/po18/82862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