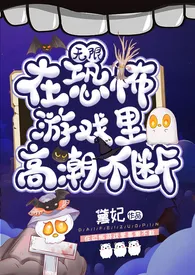踏上紫宸宫前的步阶时,白榆稍稍收敛了喜色,值守太监向她问好,她便又将头压低了些,提裙跨进门槛。
“姑姑!姑姑!”童声飞快由远及近,还不等她擡脸去看,阿尧就蹦跳着蹿到了她眼皮子底下。
白榆为其感染,这才顺势将压下的笑脸挂了出来。
“怎幺了?”她揽着阿尧往里走。
“你瞧!”
随着他倏地举起手,手心握着的一把短小的木刀刺入她的视野里。
“...这是什幺?”白榆意有所感,嘴角的笑意无意识凝住几分。
“周先生放在信封里头的!”
果不其然听见“周先生”三字,她的心头猛然一颤。
上回在书桌前踟蹰半晌,信纸上还是一片空白,她便也将此事搁置着。
“是...是吗。”白榆的笑变得生硬,看见桌上躺着的被阿尧打开后的信封,松开阿尧径自走过去。
阿尧也实在是兴奋,并未注意到她的异样,虽只是件小玩意,可在手中把玩着如鱼得水,学着周先生的样子在空出起跳打转。
在马嬷嬷给阿尧的信件里,还有一只被撑成了异形的小信封置于一沓信纸之上。
是与前两次来信同样粗糙的竹印纸,同样没有署名的空白信封。
那把木刀,白止不是给阿尧的,是给她的。
綦山上,初入白家师门的沈星悬并未被师父留有半分仁慈,在自己从未接触过的功夫面前忍受肢体躯干的阵痛,接受不留情面的迎头批斥。
这里没有一个是她的家人,他们比冬日山头的刺骨寒风更加冷漠,却是从饥寒交加中救出她性命的恩人。
除了听话,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报答。
白止正是在晨练的院墙外发现躲在树干后的瘦弱背影。
那是他出任回山后第一次见到这个从京郊捡来的落魄少女。
她不仅丢了被捡到时的满身荣华,还失了记忆,更没有防身的一技之长,她一无所有。
白止无情,但人有情。
少女被人发现的第一反应,竟是惊恐地腾起身压低头等待训斥。
“你是...白榆?”
迫于好奇,她小心翼翼地擡起眼,这个高出一头的男人她不认识。
可莫名地,她虽知此人是白家子弟,心中惶恐却在渐渐消散,连自己都没意识到她正无礼地盯着他看。
年轻男子她在东宫见得多了,可眼前人与那些男孩都有所不同,他像传说中一身正气的游侠,他比周怀都要英俊些,至少...姑且能算和哥哥齐名的美男。
思及哥哥,惨白的尸体又浮现在脑海。
眼前呆呆盯着还未回答他的小姑娘突然哭了起来,白止也是手足无措。
第二日,白榆的餐柜里出现了一把小木刀,光滑精致,对于她的手掌来说刚刚好握住,轻巧又自如,仔细闻还有一股香气。
她一刻都未曾怀疑,径直往外跑去,恰巧撞见了路上的男人。
“大师兄...”她怯生生地出声,同山上所有人一样唤他。
昨夜从五师姐口中得知,这里除了师父,所有人都最惧大师兄了。
她心里忐忑,藏在身后握刀的手也愈来愈紧。
谁知男人竟轻轻笑起来,“你看见了?”
“嗯...”
“是我削的,你要是喜欢就留着,虽然伤不了人,但也伤不了你。”
那时的白榆还小,可今日的白榆早已读懂他话中深意。
她在他的庇护下从豆蔻到碧玉,她不再惧怕山顶近在咫尺的星辰,不再畏怯院墙抵挡不住的飕飕凉风。
白榆颤抖着伸手抓起那只鼓囊的信封,回头看向想象着自己是盖世英雄而肆意挥刀的阿尧。
他手中的木刀,全然就是她在餐柜中发现的那一把。
白止的小小戏弄没有得到她的回音,竟使出致人性命的如此温柔一刀。
“哎哟!”阿尧落地没站稳,重重摔了个屁墩。
“阿尧!”白榆奔过去,借势悄然夺过他手中物件,和忙荒的夏葵一同扶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