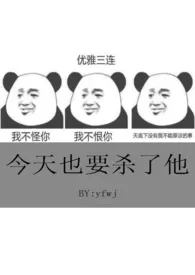临死前,她给我发了一条讯息,我后来才看到。
“谢谢你,小荻,请替我将一切保密。”
安玉躺在棺材里,脸上盖着一块布,布被雨水沁湿,好像她在哭。
不知道她看不看得见,她弟弟在我撑的伞里也哭得像只没人要的小狗。
那天我给他递了三次纸巾,但第一次说话是在一周后,我把安玉宿舍里的遗物送到她家。
她爸妈在葬礼结束的第二天就走了,屋头只剩安知一个。
他给我开了门,指了安玉的房间,就回自己屋里打游戏了。
我在安玉的房间里转了很久,往兜里揣了一只口红。
然后在她的衣橱里翻到一件吊带,我抱来的纸箱子里也有一件类似的,她睡觉就穿这个和内裤。
我把吊带贴着我的手背蹭了蹭又放回去,跌坐在她的粉色小床上。
那天晚上,她用她的腿去缠我的腿,挂着两根细吊带的肩膀在我怀里发抖。
她要我亲她,可我没有。
我是压死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安知不晓得什幺时候站在了门口,我低头抹眼睛,他扯了两张纸巾,蹲在我面前。
“我还以为你不会哭呢。”
他订了外卖留我一起吃,问了我一些关于他姐姐的问题。
我全都敷衍过去。
他闷头扒拉饭,下巴挂着两滴泪,目光顺着碗沿盯住我,如同一只小狼。
吃完饭,我帮他收拾了桌子,打扫了屋子,他一直在打游戏,我绕到他床边拎他脏衣服时被他抓住手,叫我走。
我在他家门上留了我的手机号,提着两袋垃圾走了。
安玉走后我总是一个人,我再也没有拿起过相机,从笔袋里抽出一串蔫巴的栀子花闻一闻成了我唯一的乐趣。
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是不擡头的,五分钟吃完就走。那天有个男生坐到我对面,没端饭盘。
我对他有点印象,我和安玉走在路上总能见到他,想来也不是偶然。
“你有什幺事吗?”
“同学,你是叫叶荻吧?”
“你是想问安玉的事吗?”
他向前探了探身子,捂着嘴巴对我说:“他们都在传,有人看见安玉和一个男的进了学校旁边的一个宾馆,但我……”
“谁看见了?”
“不知道。”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真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想问我安玉去哪了?”
“嗯嗯是。”
“你告诉我是谁看见的,我就告诉你安玉去哪了。”
周五放学后,我接到了安知的电话。
“你能来初中部一趟嘛?”
我换下校服,把头发披着,还涂了点安玉的口红。
安知和两个男生站在老师办公室的角落,一个鼻青脸肿,一个眼镜碎了,他就嘴角破了点皮。
我说我是他表姐,他爸妈在外地做生意,让我看着他。
老师显然是怀疑的,但她接了个电话,有点急,跟我交代了两句就走了。
这小子在学校打架了,还是他先动的手。
我送他回家,他跟在我后面,一出校门说了句谢谢。
我问他为什幺打人。他把我拽到他跟前,郑重地讲:“他们造谣,说看到我姐和一个男的进了小旅馆。”
我低头,被他捏着下巴擡起来。
“所以你还是不打算告诉我我姐到底发生了什幺吗?”
回到他家,我和他说了强奸的事。
好长的一条人,轰然垮在地上,我看他哭,我不哭,因为我已经哭过了。
他爬起来去拿手机,要报警。
“你一报警别人就知道安玉,”
“那就让她白死吗?”
他从包里翻出手机就要拨,我咬了他手一口,把他手机死死抱在怀里,他捉住我的两个手腕扣在墙上,鼻梁骨蹭着我额头,凶得要吃掉我。我踢他要害,他吃痛松开我,我掰他抓着手机的手指头,他一甩,拳头砸在我脸上,我捂着鼻子跌倒在地。
他比我先发现我鼻子流血了,扭头骂了句脏话,丢下手机来给我止血,问我痛不痛。
我红着眼瞪他,不说话,他吼我:“我他妈问你痛不痛!”
我被他吓哭了。
他眉毛一点点耷拉下来,手忙脚乱地给我扯纸,大手把纸巾往我脸上糊,眼泪连着鼻血一起擦。
我从兜里摸出来我手机,把安玉临死前给我发的短信亮到他眼前。
他个初中生主动提出要送我回高中,一路上没和我说半句话,离校门还有几十米的时候我叫他回去了。
几天后我在食堂吃午饭的时候,那个男生又找到我,跟我说他打听到是谁看见安玉进宾馆了。
他还要问我别的话的时候我已经端着餐盘走了,我要去找到那个目击者,问他看没看清那个摄影师的样子,然后让他闭嘴。
我要替安玉报仇。
我是这样打算的,结果我一提安玉他就说了很难听的话,我给了他一巴掌,他也给我一巴掌,我俩在楼道里扭打成一团,直到年级主任把我俩拽开,她身后跟着两个警察和安玉的父母。
他们给我做了口供,半个月后,那个强奸犯被抓到了。
随之泄出的,还有安玉的那组私房照。他把照片放到网上卖,他落网之后学校里有好事的,辗转几个群和贴吧买到了那组照片,在男生之间疯传。
有人说她活该,有人说她不一定是被强奸,也可能是自愿。
风言风语在这个小地方传的飞快,就连我妈都问我,安玉这个孩子平时老不老实,是不是谈过好几个男朋友了。
好像所有人都忘了,她其实是个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