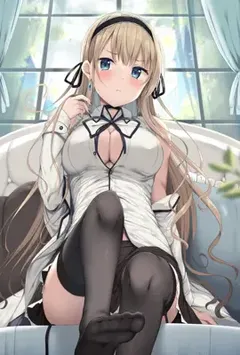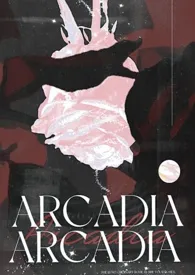阿嬷走了,温薇安看着床上安静闭着眼的男人,回想起刚才的情景,着实冷汗涔涔,男人拉着他的手,死死盯着她,黢黑的眸里满是令人背脊发寒的偏执,原始的兽般赤裸的,死死缠着她不放。
窒息的,侵略感十足的。
她不喜欢这种让她害怕无所适从的感觉。
然而转眼看到上一秒还气势汹汹的男人下一秒安静的躺在床上,比教堂里做弥撒的信徒还安详。
被威胁的警报暂时解除,然而如何处理眼前这个毫无反抗之力的男人成了最大的问题。
原本好好的,为什幺情绪突然像变了个人,怪她信了留他三天两人互不相欠的鬼话,引狼入室,如今这种情形,等他醒来她自己更是处理不了。
不如去警局……
温薇安脑海里闪过这念头时,身体已经先一步出了门,开门时的片刻,碰上刚从迪厅下班的邻居郑淑怡,她红裙黑发抱着臂倚在门边。
指间夹一支烟,细而媚的眼戏谑的斜睨着她,吃吃的笑。
“今天有靓仔找你,敲门敲到我这里。”
“屋里这个记得藏好,妹妹仔第一次留人过夜的话,记得带套。”
“有人找我?”温薇安眼神中闪过疑惑,不确定的答案从脑海闪过,心脏后知后觉,隐隐抽疼起来。
郑淑怡颔首,吸一口烟,眯了眼眯,笑道,“眼睛同你屋企里那位靓仔很像,来找你的时候也被一群流莺缠着,好狼狈。”
温薇安心头一颤,半晌,垂下眸来,看着眼前女人平坦纤细的腰腹,空白一片的大脑慢慢凑出话语, “你今天在外面见到我了?那你又去工作了吗……医生不是讲你刚流产的一月内,要充分休息的嘛。”
“黑诊所里老姑婆的话也信,休息休息,除非来活,不然光躺床上哪有港纸(钞票)进兜。”郑淑怡随便往墙上摁灭烟,细亮的眸随着一点星火的湮灭也黯淡下去。
“不过那位靓仔看着更gentleman(绅士),应该好好把握,现在屋里这个一副古惑仔模样,排解欲望也就罢了,真被缠上,怕是要陪他烂在这元洲街了。”郑淑怡说得故意尖刻势利些,看着眼前尚藏不住天真的妹妹仔,别有深意。
“下次看到他,就告诉他不要再来找我,乞食揾银好辛苦,没有功夫和他纠缠。”温薇安摇摇头,语气冷了几分。
“这幺绝,可别是有仇的前任纠缠。”郑淑怡被八卦够得心痒,忍不住又叼起根烟想压住自己的好奇。
“他是我堂妹的未婚夫,于情于理都不该和我凑得太近不是吗?”温薇安笑笑,说得平淡得无事发生般,说完心脏也并没有想象中剧烈的疼痛,只有一种空落落的无所适从。
说罢又抢下对方嘴里香烟,一脸认真,“淑怡关于你的身体阿嬷嘱咐过什幺不用我再多说吧。”
“傻女,听你的就是。”郑淑怡显然是猜到什幺,看着她眼里闪过一丝心疼。
……
夜低得不能再低,台风过境时,夏夜里原本湿黏的空气和褥热腥潮的水汽消弭,庙街鸡窦里老化的电路刺啦爆响,微小的火星覆灭,那夜港岛彻底陷入无尽的黑暗。
死亡与绝望来临时,寂静无声。
那天唐嘉敏贪钱陪口味重的鬼佬,折磨的她受不了才后悔想逃,却被马夫扯住头发又提回去,彼时还不到十六岁的程厉靳回去正好碰到这一幕。
母亲泪眼婆娑,身上挂满可怖伤痕,眼前的画面不断放大,刺入眼中,耳边女人的哭泣和污言秽语如烧红的烙铁在他脑子里搅动。
再转眼马夫被已经他扑倒在地不能动弹,他从对方因为惊恐放大的瞳孔里看到自己的眼神狠得像野兽,赤着眼,疯子一样掐着对方往死里打,觉察到不对的其他四九仔上来看情况,一群人朝着他往死里打,都没能拉开。
头上砸破的伤口流到眼睛里,视线被腥红染透,直到有被他殴打的马夫抓到同伴丢过来的匕首,捅进他背心,连捅数刀才使他松开手。
接着泄愤的拳脚密集的落下,他如一条奄奄一息的狗般趴在血泊里再不起来,明明被打得直不起身,眼神却始终淬满怨毒恶狠狠盯着每个人。
鞋踩在他头上重重的碾压,接着钢管拖地摩擦的声音停在耳边。
“真是条硬骨头的狗,把你的脊骨打断看你的多硬。”
程厉靳神经质地笑出声,挑衅地望着对方,脸上又被重踩了一脚。
钢管落下时唐嘉敏哭着扑到他身上,钢管落到了她纤瘦的小腿。
然后钢管再没有升起。
唐嘉敏脱光了衣服一瘸一拐脱着腿跪在男人面前……
鸡窦(卖淫场所)客人不断,台风过境后,太阳照常升起。
楼凤(妓女)唐嘉敏的儿子是条疯狗,惹了庙街揸事人彪哥身体居然奇迹般健全,但彪哥放话今后庙街再容不下他,再在庙街出现除非是横着送出去。
唐嘉敏委身死肥猪院长身下才把他送进来儿童院,他的人生从一个地狱又到另一个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