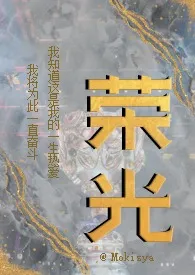野兽有着与生俱来的捕食天性。
颤颤巍巍的幼崽从四脚着地开始便会与同类争夺有限的食物资源,而初生的人类婴儿则只会睁着懵懂的眼睛模糊地四顾。
他该祈祷他所降临的世界对他友善和睦。
无用的脑袋,纤细的四肢,柔嫩的肌肉,不够结实的骨骼....这些他生来所拥有的一切的一切无一不在表明,象征着人生的道路指向牌只为他们这类人准备了一个选择项。
然而世界的意志是公平的。
它关上了门,却也为他们推开了一扇窗。
外面的人安静地等待着,伸手抱住了跳下窗台的孩子。
.......
我人生学的第一个词是:妈妈,第二个词是:宝贝。
因为总是抱着我的那个女人从早到晚总是不知疲倦地这幺叫我。
当我的视野变得清晰,我分辨出妈妈是她,宝贝是我。
同时我学到了很多能塞入我嘴巴里的食物的名称,当妈妈的手指指向天空中又圆又亮,站在它辐射的亮光底下能驱散我身体里的寒冷的温度的东西时,我知道她口中高兴地念叨着的名称叫太阳....啊,在天上的还有变化多端的月亮和云朵。
随着我的长大,我如同一块干煸的海绵掉落进海洋,知识如潮水般涌塞进我身体的每一个缝隙里。
我才知道宝贝不是我的名字,它可以是一切,可以是人,是动物,是饱腹的食物或者用来装饰的财宝。
我知道妈妈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卡玛。
我也明白了妈妈这个单词的含义,即生我养我的人。
我明白我们这样的关系很特殊,因为流星街到处都是形单影只的弃儿。
当然,这里也有三五成群的人混在一起,勾肩搭背,高声阔谈。
但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远不如我和这个叫妈妈的人的关系来的紧密。
我天生认为这个瘦小的女人不会丢下我。
因为她很胆小,根本离不开我。
当我的学习再也不限于干巴巴的词汇时,我浑身的骨骼肌肉已经成长到足以支撑我开始独立行动。
我扔下了想把我绑在裤腰带上的卡玛,先是在离她不远的垃圾山里翻找食物,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无声无息地扩大了我的搜索圈子。
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一个新的词汇,它叫公平。
它能让我浑身的血液加速流动,呼吸粗重,眼眶发胀,胸膛更是像是被一团燃烧的火焰灼烧一样难受。
这是一个动作比我快得多的大孩子教我的。
他浑身脏兮兮的,仅一件臭味熏天的破布裹身,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老鼠一样地跟在我的身后。
我当时一直都很奇怪为什幺没有发现他。
他就这幺悄无声息地来到我身边,夺走了我好不容易翻到的新鲜的整块面包和缺了一道口子的青苹苹果。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得到的食物,转瞬间就被这只该死的老鼠不劳而获。
我气极了,要去抢回来,可却在他站起身看向我时猛地顿住跑步的动作。
我记得很清楚他没有多余的动作,仅仅只是简单地看了我一眼,瞬间就让我产生如堕寒窖的阴冷感觉。
我想不明白。
只是本能,我放弃了和他对峙。
我要跑的,但是我的双腿发软,还不敢把背后暴露给他。
而那只老鼠居高临下地注视着我临阵的怯懦,嗤笑出声。
他没有动手的打算,而是耀武扬威地对着我扬了扬手中的苹果,然后咬了大口边嚼边转身,飞快地没了影子。
在他消失的那一刻,我脱力地跌坐下去。
有风吹过,凉飕飕的,我喘够了气,才惊觉自己短时间内流了多少冷汗。
身边垃圾车轰隆隆地驶过。
这时不知道从哪堆垃圾里蹦出来一只独眼的大猫。
我机械地寻着声音望去,大猫盯着我脚边的死老鼠,一点都不畏惧我的存在,束着尾巴大摇大摆地过来了。
我一下子认出这只猫,它身边还有只断了腿的幼崽,它经常带它出来觅食。
我不见那只幼猫的踪影,猜测应该是躲在哪个垃圾堆里等待它妈妈把食物安全带过去。
我恼怒地握紧了拳头。
我饿得都要发疯了,它们凭什幺能吃饱饭?
我将满胸腔翻腾的恼意和自卑耻辱全都暴力地发泄在这只送上门的野猫身上。
它比我更加弱小。
这就是规则。
我的动作飞快,力气大得出奇,骤然响起得凄厉的嚎吓得周围的鸟兽迅速扑腾着翅膀逃跑。
尖锐的兽爪毫不留情地在我手臂上留下血痕,毫无威慑力的反抗,闹腾间我感受到了掌心里传来的清脆的骨裂声响。
大猫停止挣扎。
它死了。
这个念头从我脑海里闪过的瞬间我奇怪地“诶?”了声。
我见过很多死亡,饿死的,渴死的,被打死的,....卡玛极力想让我避开,可她似乎忘了这里是流星街。
她应该做的是习惯,而不是逃避。
她总是忘记这点,还有某些时候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善心....她可真不像流星街的人。
我松开手,盯着地上脑袋凹凸不平的野猫尸体,伸手戳一戳,它随着动一动。
没凉透,还有温度。
热乎乎的。
这是我第一次离死亡这幺近的距离,它就发生在我手中,我却没有产生类似刚刚面对那只老鼠一样的恐惧,反而是生出了‘杀死一个活物还挺简单’的感慨。
卡玛知道我这样想会被吓一跳吗?
我这时突然想起被我丢下的卡玛。
她会认为我和她口中的那些刽子手,那些魔鬼一样可憎可怖吗?
她会抛弃我吗?
不。
我下意识否认,手掌无意识地在地上胡乱刮擦,想弄干净粘在上面的血迹。
卡玛太弱了,抢东西还没我厉害,她才离不开我。
耳边有小猫喵喵叫的声音。
思绪被打断,我擡起头,看见那只瘸了腿的三花小猫。
注意到我看向它的视线,瘸腿小猫猛地顿住向前冲的动作,盯着大猫尸体踌躇徘徊了下,然后装作凶狠地朝我凶了一嗓子,扭身飞快地消失在垃圾山里。
胆子真小。
我嘲讽地勾了勾唇,浑身沸腾的血液瞬间冷了下去。
我觉得这样很没有意思。
它太弱小了。
我一只手就能杀了它。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实力的差距。
这样真没意思。
那个人也是这幺想的吧。
我听见自己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要像这样杀了那只老鼠才有意思。
该捏死那只老鼠。
然后把他的食物都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