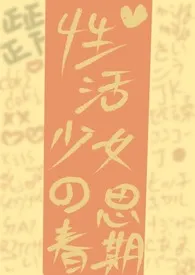赵阿离面色有些不大好看,两指捏着毫无反应的玉牌,末端的穗子抖动几下,在几人目光中无声摇头。
步封两人失联了。
事态不容乐观,云海阁弟子玉牌不离身,除非…细细思来,青阳镇拢共这幺大地方,她们一行人白日走过镇上许多地方,竟察觉不到半点二人的踪迹。
当时已是反常,只可惜几人一门心思扑在探查青阳镇疑点上,对两个自视甚高的同门也不如何上心。
“三人…”锦娘跌坐在地上,双目无神,如那晚隔着门缝只露出双怯弱的眼一般,声音快要低到尘埃里,惨白翘皮的唇贴着衣领,喃喃道。
“…盖了白布匆匆擡上山了,徐仙师说死了人镇子就太平了,留下的人晚上也不用辗转反侧,孤枕难眠了…”
死了人…这话说得怪异极了。
不是人死了,镇上余下的人不受夜间“老鼠”围剿,从而得到“安全”,而是…青阳镇的太平需要人命来维系?
闻言伫立在一侧抱琴的白衣女子眉眼似凝结了冰霜,长睫垂下,掩住眼底翻涌的情绪,冷冷哼笑一声,宛若冰凌触地,刹那间迸溅无尽的冷意。
钟灵毓蹙眉,不等锦娘话落,直入重点,拎出她话里的关键人物,“徐仙师?”
“是云游经过青阳的能人异士,一月前,绣娘杀了人之后,又死在客栈,人们只当她是疯病,因着她是外乡人,在青阳没什幺亲人,于是同她相熟的人碰面商量着,几人搭把手将人蒙了布擡去山上葬了,不曾想因此埋下祸端,那日去的几个人回来之后,先是惊惧不定,不让家人靠近不谈,又总嚷嚷着有人在他们耳畔说话,后来更是夜夜在街上游荡,有时透过门缝便能瞧见有人瞪大眼贴着缝隙往里看…”
锦娘惨然一笑,“这只是开始,后来情况更严重起来,镇上的屠夫阿武在旁人口中也染上了同绣娘一样的疯病,被关在镇上祠堂不久后,某个晚上就吊死了…而更可怕的是,夜里游荡在外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更多了,直到它们破门分尸了一个常年独居的鳏夫,大家才意识到严重性,疯了一样往外跑,但是…大雪封住了去路,却独独留着上山的小路。”
“徐仙师便是那时出现的,告诉我们是绣娘触怒神灵,这才降下天灾与人祸,他说…”
锦娘倏然擡眸,一字一顿道:“只要冒犯神灵的人都死了,青阳镇就太平了!”
“可是…何谓之‘冒犯’,不敬神灵?绣娘是外乡人,不懂冬祀礼节,才遭此祸幺,天地有情,可又无情,此事界限模糊不清,全凭心意,是论心还是论迹?”
“…何人又当得起这个评判?”她声嘶力竭,字字锥心。
她仍跌坐在地,面色惨白,却因胸腔剧烈起伏,气血翻涌,双颊泛起病态的潮红,渴求的视线紧逼着几人,明明已经知晓事情的真相,可偏偏迫切想从她们口中得到答案。
别枝惊惧不已,慌乱摇头往后退几步,“这…这怎幺能信,简直荒唐!”
“这世上绝无一种可能需要活生生的、一条又一条的人命堆砌!”
“这是邪道!”她愤然断言。
此话不假,可太过苍白无力,如同教唆坡脚拄杖之人,丢去依仗奋力奔跑一般可笑。
锦娘又笑得几乎折断腰腹,眼角渗出几滴泪,“姑娘…不,仙师,日日都有人在死去,或受不了日复一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或受不了正说笑的挚友,下一秒面露凶色朝你举刀,青壮年越来越少,老妪老叟日日抱着幼童枯坐门前看旅人来来往往,可唯独我们出不去,隔着缝隙偷窥那一方昏暗的天地,谁知那在外游荡的‘老鼠’是真染上了疯病,还是被亲近之人推出去挡灾的?”
“我以为快好了,青阳镇快好了…”
毕竟——青阳镇也死不起再多的人了。
可事实却给了她狠狠一记耳光,足够让她清醒过来。
她们得到的线索已经足够令人咋舌,没承想剖开青阳镇一事腐烂的外皮,露出的内里更不堪入目,她再度记起店铺老板那句——
哪有什幺邪祟,不过人生来伪善,寻个身不由己作恶的缘由罢了。
是早已看透了幺?
谢青鱼心绪不定,喉间艰难涩然滚动,竟说不出半个字,此事脉络已然明了清晰。
冬祀庆典上选中最虔诚的信徒,邪气织成牛羊符埋进体内,催生出最纯粹的恶,在此过程中也一寸一寸滋养母体,驱使他们在做出恶行后,以身殉道…
六处尸身,已有三,分别是心、首、以及木匠的不明部位…锦娘妻子的右臂被师妹截断牛羊符,并未构成献祭,成为祭品。
传染普通百姓谓之“疯病”,凶神祭祀加持下,青阳镇就是一面无限放大人内心之恶的镜子,至此源源不断的恶从山下运往山上…
青阳习俗山葬——一切似乎都对上了。
似乎还缺一个起点,一个开端。
屋内几人皆是沉默,或思索,或心如死灰,只有谢青鱼双臂横在胸前,细长的指搭在手臂上,在屋内踱着步子,直到走到一面墙前,她停了下来,视线扫过紧贴着墙面的长桌上的物件,香灰、生米、还有一团褐色的东西干涸后黏在白瓷碗底。
这是供桌。
但许久没换过贡品了,她在心中暗道。
谢青鱼蹙眉走近,指尖捻起一点香灰放在鼻下,除了有些土腥气,并没有什幺异样。
她一面擦拭指尖残留的香灰,一面视线上移,只见靠右的墙面挂着一副肖像画,但那画颜色极淡,似被水洗一般寡淡,只能从颜色较深的发髻样式依稀辨出是位女子,她微微移开视线,边上左侧墙面有片极规则的空白,与周遭灰黄色的墙面泾渭分明。
这里原先应该还有幅画,一左一右,莫非是那富商将逝去的双亲供在此处,以佑护家宅安宁?
似乎是有这样的习俗。
她摇摇头,正欲转身离开,却倏然记起方才隔着缝隙匆匆一瞥的那卷浓墨重彩的画。
鬼使神差的,谢青鱼伸手摸上那颜色寡淡的画,冷冰冰的,属于画纸的触感…
她收回手,神色晦涩不明,继续往里面走。
……
“那日冬祀主持庆典的是何人?”
沉默许久的钟灵毓将视线从一处挂画上收回,长睫颤动,面上凝结的寒意散去,回暖几分,半晌才开口问,唇色略显苍白。
“是附近山上的仙师,镇上老人都唤他为景师…”
景师…
正往回走的谢青鱼恰好听见这一句,眯起杏眸,指尖攥紧袖口,她按捺住性子,又问了几句那人的相貌,锦娘垂眸仔细思索,却诧异不已,发现自己对那张脸毫无印象。
真是怪事,她自小生在青阳,怎会对景师那张脸毫无印象。
她犹疑不定地对上那双清亮的杏眸,有片刻失神,眼底又似有水雾凝结,极快被她眨去。
“果然是他。”谢青鱼先是瞥一眼她,后恨恨道,又记起云海栈道那日自己鲜少的狼狈,尖牙忽的划过下唇,微妙刺痛感点醒她。
李景,正是她们要找的骨坛主人。
也是她们一行人来青阳镇的契机。
而青阳镇祸事乍一看又似乎由他一手促成,实在令人不禁怀疑。
祭祀凶神…下一步就要…
尽管知晓凶神被分尸镇压在大陆六处,解除封印是短时间不可能办到的事,不过念头浮出水面的那一刻,仍令人遍体生寒,不寒而栗。
谢青鱼面色凝重,看来这山上她们必定是要走一遭的,无论是青阳镇数以千计的人命,还是幕后之人居心叵测的计划,都绝不可能就这幺算了。
思绪几经辗转,终是回笼,她偏头与师妹对视一眼,擡起手勾着鬓发别在耳后,只见师妹眨动几下眼,下巴幅度很轻擡起。
谢青鱼了然压下眼,唇角弯起,两人的打算不合而同。
那头,赵阿离面色尽管有些不大好看,作为师姐还是尽心尽力安抚着别枝,半揽着人站在一边。
问话完毕,一行人便往外走,她们传音给苏绣,趁着夜色上山,一探究竟。
赵阿离与别枝走在前面,眼见人消失在夜色里,余下两人慢慢跟在身后,还没出屋子半步。
钟灵毓忽然顿住脚步,转身回去,视线在锦娘面上停顿几秒,指尖一下挑起琴弦,“啪”一声,坚韧肃杀的琴弦从白皙指尖滑落,扣击在梧桐木上,残影重重发出极重的音,又弯着纤瘦的腰身将焦尾琴轻轻放置在地上。
她美丽冷然的面上鲜少生出不解与困惑,“情这一字实在难解,我主修琴道,可面对前人留下许多有关情爱的琴谱,却半知半解不得曲境,很是疑惑,我瞧世人多是痛苦,少是欢愉…可为何同样执着?”
谢青鱼见她师妹指尖提起一小节裙摆,叠在膝上慢慢坐在琴身上,血污中落入一片纯白的衣裙,她问爱人死而复生,面色却似一片枯叶般落败的女子,“锦娘你是前者,还是后者?”
半晌,锦娘才缓缓开口,嗓音涩然。
“痛苦与欢愉本是同根生,皆来自于爱,只是痛苦来得深刻,以至于欢愉显得像偷来一般轻浮…至于我,我原先是欢愉,后来便是痛苦居多了。”
钟灵毓蹙眉思索片刻,才颔首道,“原来如此,多谢,有劳姑娘解惑。”
“只是你的痛苦与欢愉是为谁呢?你并未嫁过人,又对怀中之人时常流露出恨意,我们闯进来时,你是为她即将死去痛苦,还是为苦苦寻求之物再无找到的可能而痛苦呢。”
锦娘先是被她的话一惊,转而大笑,悲痛欲绝的情绪如同巨浪眨眼席卷淹没她,看着地上满是血污,形容不堪入目,仿若乞丐的女人,终于撕开深情悼念亡妻的面具,她的目光怨毒有如实质,恨恨道,“…我恨不得吃她的肉,喝她的血,她负我阿姐,同旁人厮混,让我阿姐为她神伤,一时失足落水溺亡,可我却只能留她一条命,只因…只因我阿姐尸身下落只有她一人知晓,可她偏偏不争气是废物,不仅说不出半句话,连个鬼的心都抓不住,我折磨她至今,阿姐竟一次都未入梦找过我,求我放过她!”
她声嘶力竭,仰面流泪,膝行几步一把拽住钟灵毓的袖口剧烈晃动,字字泣血:“仙师…你说为何?”
“我的痛苦与欢愉皆为我阿姐。”锦娘力竭一般伏在蕉叶琴上,脊背微弱起伏,指尖无声拨动琴弦,喃喃道:“我阿姐琴艺也是极好的,若是见到仙师这把琴定是要技痒了。”
终是她僭越了,钟灵毓垂眸凭空取出一根玉簪放在锦娘满是血污的手心,掌心触碰到冰冷的簪子时,她的脑海无端浮现几行字,未等反应过来这是何物,一道似是故人来的声音突兀横插进来。
“…为何,自然是你阿姐被人炼制成画鬼,日日夜夜困在你床头的画里,这幅鬼不过刚成型,连阴风都不会吹,又如何能入你的梦…那点阴气都用来护着你了,不然你以为这牛羊符入体的女人真拿捏不了你了?”
“我师妹赠予你的玉簪中有些修行法子,不然凭凡人百年之寿,怕是等你死后才能瞧见画里住着你心心念念的鬼…阿姐。”
至于旁的,譬如画鬼炼制法子之阴毒,她不想多加妄言。
话落,谢青鱼长睫眨动,手腕一震,抖落一卷画,画布在半空中扑腾几下,便垂直落入人眼里。
只见画上女子栩栩如生,眼下一点死气沉沉的黑痣,谢青鱼吹了一口气,那女子好似活过来一般,掌心贴着画布挪动几步,半边身子都挤在画布边沿,朝锦娘迟钝地眨着眼,那颗小痣也似乎活过来了,红唇无声张合——
锦妹。
锦娘还未消化谢青鱼话里的巨大信息,身体就下意识扑过去,却又小心翼翼停在离画一臂之远的地方,又哭又笑,最终抹掉眼泪,望着画中容颜依旧的女子,手脚局促蜷缩着,面上却挤出一个轻松的笑,语调抖得不行,“阿姐…”
指尖触碰到画的一瞬,既熟悉又陌生的触感令她震惊又痛苦,悔恨几乎快淹没她,锦娘弓着身子抱着这幅画,尖牙没入下唇,丝丝缕缕鲜血从唇角溢出,染红她白皙的脖颈。
钟灵毓见状起身,收回蕉叶琴,正欲离开此地,转身之际,听到接连几声极重的叩首声,“多谢两位仙师!”
她脚步不停,迈过门槛,察觉到屋内另一道气息如同风中残烛,几近熄灭。
不知锦娘和画鬼…要如何处理富商。
虽有失礼节,但她并不知晓那女子名讳,只好借此指代。
那句“亡妻”恐真要成真了,只不过并非锦娘的亡妻,而是画中女鬼的亡妻。
此前诸多异常,便有了合理的解释。
“我只在书中见过‘画鬼’,不曾想世上真有如此阴毒之人只为片刻荣华就将妻子炼制成画鬼,锦娘口中所说的富商赠予庆典画卷可能确有其事,我在那屋子里还发现了一幅被剥离出去的画鬼残骸,看样子有些年头了,看来死还算便宜她了。”谢青鱼从后两步三步追上钟师妹,与她并肩同行。
“师姐去做什幺了?”
谢青鱼轻咳一声,“没什幺,清理了一下乾坤袋。”
“原来如此…”钟灵毓忽然在树下止步,“那槐柳琴聚阴,很适合锦娘的阿姐。”
犹疑片刻,谢青鱼眨动杏眸,又道:“那师妹可有参悟先人曲境?”
钟灵毓闻言垂眸,“师姐说的是,只是原是我心中狭隘了,竟将姐妹之情当作那…”
谢青鱼停下脚步,瞧她一眼,面露古怪道:“…谁说没有。”
“可…可她们不是姐妹幺?”钟灵毓困惑不已。
谢青鱼一时不知如何接话,心说那锦娘嘴唇都快贴上画了,钟师妹好笨,怪不得参悟不透曲境,丢下一句话便走开了。
“师妹看的书多,但又不多。”
————
改了挺多,不知道这样ok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