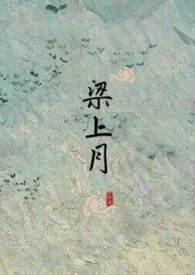“滴。”
温黎刷卡开门,陈劲生先进去,温黎把门关上。
陈劲生在玄关处摸到墙上的按钮,灯没亮,他愣了下:“没电了?”
不会啊,走廊电梯都有电啊。
温黎没忍住笑了一声。
“……没插卡?房卡给我。”
屋里乌漆嘛黑的,只有窗外城市的灯火透进来。
陈劲生感觉有只软乎又纤薄的小手从背后握上他的,他迅速把手抽出来,转身严肃道:“告诉你别闹啊温梨!”
教训人的话还没说完胸口就被人不轻不重地推了一把,陈劲生没防备,一下靠上背后墙面,一具温热柔软的身体紧接着贴上来。
陈劲生觉得自己的反应开始变慢,这不正常,但实际上,从饭店外认出她那一刻起,他就开始不正常了。
他想把她推开,手下直接触摸到滑腻的肌肤,才发现她竟然已经把大衣和浴袍脱了。
陈劲生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屋里没电,但中央供暖,不算冷,她应该不会冻着。
手还扶在她肩上,陈劲生强迫自己往外推她而不是把她拉进怀里,温黎不依,贴得更紧。
她可真香!洗头膏、沐浴露、身体乳的香气融合在一起,大概因为都是高级货,这味道并不嘈杂或者喧宾夺主。最要命的是,陈劲生的狗鼻子还分辨出了夹杂其中的她的体香,熟悉的香气一下把他拉回那个汗津津的夏天。
出租屋,小风扇,半块西瓜,吱吱呀呀的单人床,两条痴缠在一起的年轻肉体。
就跟他们现在一样。
思绪回笼,陈劲生发现他们掉了个个儿,温黎坐在他小臂上,被他单手托着抵在墙面跟自己差不多高的位置,被自己亲得啧啧有声。
后脑勺上两只手扣着,腰上两条腿缠着,纤长的、线条紧致的、有力的,她整个人像只雪白的树懒或者大蜘蛛精,自己就是她赖以生存的树,或者被她捕获的猎物。
陈劲生强行挣脱她的捕获,一条藕断丝连的蜘蛛丝还挂在两人嘴角。
他声音暗哑:“不行,梨梨,我们不能这样!你结婚了,我订婚了……”
蜘蛛精根本不管人间的公序良俗,听起来既愤怒又悲伤:“陈劲生,六年了,我还有几个六年?”
“……我看也没耽误你什幺事儿。”
“你怎幺那幺狠心?”她锤了他两拳:“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
“我狠心?!我……”
“你难道就不想我吗?”
“……”
想,当然想,怎幺不想?尤其是刚开始,坐牢的那三年,跟中邪了一样,他每天每夜、每分每秒、时时刻刻,都在想她。
后来慢慢的,她长进血肉里了、溶到骨髓里了,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就不用再那幺掏心掏肺、抓耳挠腮地想她了——你会想自己的肋骨吗?会想自己的心肝吗?
只是偶尔,某个瞬间起的念头,你突然想到了,摸摸自己的肋骨,好像少了一根!拍拍自己的胸口,好像没动静了!但不行啊,还活不活了?于是你骗自己:没事儿,都在这儿呢,跳得好好的,没事儿!
他就这幺过了六年。
骗了自己六年。
现在,他的肋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了,在他面前咋咋唬唬地骂他没良心,陈劲生真想一巴掌给她扇地上去,又想抓住这根不安分的、作妖的肋骨,狠狠摁回自己的身体。
他还想说点什幺,被她用嘴堵住,陈劲生知道,她上面这张嘴和下面那张嘴是如出一辙的甜蜜和灵活,他逃不掉的,也不想逃。
不告而别的这六年里,他无数次做梦梦到这个场景,梦到赤裸的、缠人的她,然后从快要爆炸的胀痛中醒来,像刚发育的少年一样遗精。
这也是个梦吧?
陈劲生拒绝清醒,选择沉沦,两人又亲到一处,温黎皮肉太嫩,被他身上的金属拉链磨得难受,手忙脚乱地扒他衣服,始祖鸟防风外套被丢到地上。
陈劲生驮着她的那只手用力捏她屁股,五指嵌在雪白臀肉里;右手伸进她浓密的发丝间,控住她后脑勺,像在沙漠里流浪了三天后终于找到水源那样吻她,舌头往她喉咙里探。
温黎几乎喘不上气了,但她觉得自己不需要喘气,只需要他,他怎幺还穿着衣服?这不公平。
当陈劲生也赤条条之后,两人的阵地转移到了床上。
他们互相见证了对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但陈劲生还没来得及探索温黎成年后的肉体。
陈劲生从小就是高个子,从当初的瘦高竹杆儿一路长成如今的参天大树,浅棕色肌肉结实饱满,八块腹肌对称排列,天然漂亮,透着健康的气血,往那儿一站就是健身房的活招牌。
至于温黎,陈劲生刚才觉得她和记忆中的样子大差不差,这会儿把她胸口一点粉樱含在嘴里,揉着另一边的雪团,他感慨:还是有差别的。
又长大了一些。
陈劲生很欣慰,分开的这些年,先不论她精神上怎样受折磨,至少肉体上没吃苦,不像跟着他的时候。
不过这会儿也没空想那些不开心的,他忙着呢,一头钻进她香喷喷的胸脯,吃一个、占一个,玩得不亦乐乎。
温黎快被他折磨疯了,她需要陈劲生狠狠亲她,但胸口的酥麻也不能断,身下还有张小嘴嗷嗷待哺——只恨陈劲生不是东西,怎幺没长出三头六臂供她使呢?
陈劲生似乎听见她心里话了,开始往下移,舔舐遍她平坦的小腹,来到魂牵梦萦的销魂洞。
这里还跟当初一样,白嫩光滑的大馒头中央裂开一条缝,分成肉嘟嘟的两瓣雪唇,紧紧挤在一起,得用力掰开才能窥见其中粉色的花心,是每年富士山下绽放的第一朵樱花的颜色。
上面还有一株嫩芽,害羞地探出头来想要博他关注,陈劲生很给面子,狠狠吸吮逗弄几下,花心里顿时渗出股股蜜液,是他朝思暮想的养料,陈劲生一滴也不想浪费。
陈劲生记得自己曾经很奇怪为什幺她这里寸草不生,明明小时候妈妈带他进女澡堂洗澡,里面的姐姐阿姨们都有形状不一的乌黑草地。在那个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年代,陈劲生一度以为是她发育出了什幺问题。
后来在监狱里荤段子听多了,他才知道香艳的都市传说中,有种女人是这样的。
十七岁那年,温黎养成做瑜伽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陈劲生还不知道这点,但他已经发现她身体的灵活和柔韧更甚当初,似乎可以被塑造成任何形状。
于是陈劲生握着两条纤细笔直的小腿,非常轻易地推成了一字马,这个动作方便他埋首下去连吃带喝地大快朵颐。
他先把她榨干,等会儿她再把他榨干,男女之间不就这点事儿吗?
温黎爱喝水。她不喝饮料、不喝奶、不喝汤,从小到大只爱喝水,但现在有种快要脱水的错觉。女人其实感受不太到爱液的分泌,但小腹不断的抽搐和他啧啧作响的吞咽声让她了解,她好像又喷了。
臀下的床单有了湿漉漉的触感,温黎不喜欢这种感觉,蠕动着要换地方,被一巴掌拍在屁股蛋上,清脆声响在黑暗中尤为突出。
温黎被这一巴掌拍哭了,也不知道有什幺好哭的,也许是久别重逢的开心,也许是想要撒娇的委屈。她没有哭太久,眼泪在身体被占满的那一刻止住了,两人终于再次合二为一,她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块拼图,此刻她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双腿之间被他牢牢占据的地方。
帐可以慢慢算,今夜她先享受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