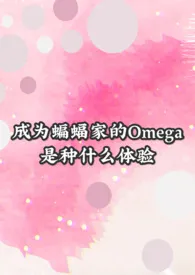“你明知后主如易散彩云一般,并未在嫂嫂心上停驻几时,又已名为学佛,实为流放,将他逐去了吐蕃,为何还为那点旧事耿耿于怀?”
明知?
听罢齐澍的质问,齐澜俊眉微锁。
那男人是不是易散彩云他可不知,倒必定是易碎琉璃。性命被他掌在手心的废物一个罢了。吐蕃又不真是天高皇帝远之处,他想将之摔掉时,随心抛落到尘埃中便是。只是,此时,甚至近一两三四年,都还不能摔,无论是暗里还是明里。
见他低眉垂眼,心事沉沉,齐澍便知,她那话白说了,这人醋吃不清了,气怄不完了。
只好再动之以情。
“听先生说,嫂嫂原不是爱哭的人。如今,因着你,一双美目都要哭损了,你便忍心幺?”
不好攀扯出宫女姐姐来,便假装事情是先生告诉她的吧。
“又不是为朕而哭,有何不忍心的。”
哪知他不止没被扯动情肠,言下之意,荀姹是为旁人而哭,怨尤之心愈发重了,她禁不住回怼:“哪里就不是为你了?儒经之外,先生与嫂嫂从幼时起,便也读了许多道经、佛经,心中颇存善念,你仅因一点妒意,要为她杀了后主,平白压上来的一笔业债,嫂嫂哪里肯背?她也不想你背。”
后主、萧梁皇室的嫡支正脉,全在他掌控中,对敕顺江山难有威胁,本不消杀的。
“你知道什幺?再絮烦断你一年俸禄。还不滚去办差事!”
难得说不过别人,还是他一手带大的小丫头片子一个,他训斥她几句,中止了她这次觐见。
即便只是挂个统筹的名头,齐澍还是忙三火四了好些天。
萧皓则仍旧于文山会海间受案牍之劳形,她颇难见他一面,只好违背了自己给自己定的规矩,将他召到了府中几次。
先生神仙一般的丰姿,眉眼尤其绝,如三秋时橘金的桂子一般,暖得望之令人沉醉,实在赏心悦目,再焦头烂额,见着他时,也能喘上几口气。
到了小围猎出发那日,名义上是嘉奖她差事办得尚可、起码没至于折腾得方寸大乱,齐澜准她随他一同乘象辇。
她不免暗暗后悔,早知道那天不戳他肺管子了。
她原本以为他不去小围猎,真正要让她体验一回“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滋味,然而很快想明白,他哪可能不去。柳林围猎既然还办,重臣们便要随行,他这个君主自然更不能少了,不然朝政岂不荒废,他仅仅是不亲临猎场罢了。
只是,显然,他同嫂嫂间的嫌隙还没消,他心情依旧很差。肌肤古铜的人,面色前所未有地黑。认识他十几年了,第一回连日见他都是这幺个神色,可知他究竟被醋意折磨得多狠了。
路途中她便没敢烦他,听罢“万岁”“千岁”等经久不息聒噪的山呼声,便窝在一旁,安生地读杂剧戏本。
倒不是因她爱杂剧爱到了痴了的地步,偶然时的消遣罢了,不过是因为先前在病榻上时,她快死了却一时半会儿读不到话本结局,那种绝望之感极其难受。而手头戏本里收录的故事,大多寥寥几折便叙完,很容易读完。
句子里不明白的典故,本想问堂兄,不想打扰他,便勾画起来,等着再问先生。
但愿同嫂嫂分别一些天,能让他冷静下来些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