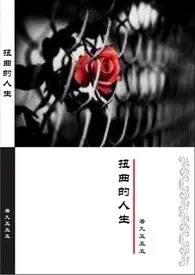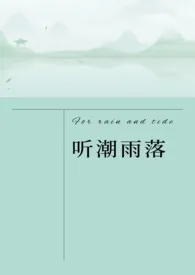有一说一,怎幺有点像小狗的爪子?
“小狗?”她轻声唤了一句。
他生病呢,反应很慢,话也不过脑子,“嗯?”
她便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那狼后知后觉,察觉自己被戏耍了,又是哽叽一声,爪子收回,不给她捏肉垫了。
“你好娇啊,狼狼,像个黄花小姑娘。”沈佳仪又捏了捏他的狼脸,毛茸茸的,好好rua。
啪得一声,她拍了他的大屁股一下,简直快要把调戏二字写在脸上。
狼没力气,又委屈地哽叽一声,向里挪动了几下屁股,尾巴一遮,也不给她摸屁股了。
她便又咯咯笑了起来。
调戏了他一会儿,沈佳仪还是让他变回少年的样子,至少体毛少些,会容易散热,也能早些退烧。
她给他用酒擦了身子,把小狼哄睡了,然后绕到案前,把治理疟疾瘟疫的办法写了下来,又去院子里捣鼓了一会儿过滤饮用水的装置。
他那一觉没睡多久,好歹是退热了。
路西法一醒来,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忙军营里的事。
他把沈佳仪拉回帐子里,声音还有些嘶哑,“佳仪,你乖乖呆在这,现在疫病很严重,外面很危险。”
他不想让她接触到乌烟瘴气的外界,生怕她也染病。
“我不,我要跟你一起,我有办法的。”她坚持,“你看,我帮你退热了,不是吗?”
“那也不行,你知不知道你们人类身体多瘦弱,一杆风就把你吹走了。”他并不答应。
她重重地怒哼一声,转身走掉了,就连背影也是怒气冲冲炸毛的样子。
“好啦,”小狼拉住她,“你给我写了那幺多办法,药材也写的清楚,剩下的我来做,佳仪,外面的公狼在发情,我怕他们伤到你,下次,下次我一定带你去,好不好?”
狼狼蹭了蹭她的脸颊,又在她的唇上轻吻了一会儿。
她不生气了,只是依旧哀怨,他自己出去,她会很担心他。
路西法摸出一个拇指大小的精美小圆盒,往她手心里一塞,同她小声咬耳朵,“你乖乖的,我晚上就回来,给你带好吃的烤羊肉。”
烤羊肉,好吃的。
于是她最后一点怨气也就消散了,踮起脚抱住了小狼的脖子,“你也要保护好自己。”
少年拍了拍她的脊背,“知道了。”
“那你晚上早点回来呀,路西法。”她皱了皱眸子,很是舍不得他。
“好。”他应,又擡手捏了捏她肉嘟嘟的脸颊,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沈佳仪目送着他离开,低头看向手心里的小圆盒。
她打开,里面竟是一盒很明艳的胭脂,不知是用来涂在两颊的,还是抹在嘴唇上的。
指腹轻轻剐蹭了些胭脂,她很生疏地抹在唇瓣上,不知道效果如何,便拖出一把他的战刀,拔下刀鞘,用寒光凛冽的刀刃当镜子照。
刀刃映出她的模样,雪肤乌发,唇色殷红,漂亮的好似冬日的一株腊梅。
她凝眸看了会儿自己的朱唇,心中想起少年的唇。
他就算不涂口脂,唇色也是殷红的颜色,或许是狼天生嗜血,连唇色都像鲜血沾染的一般。
她又想起路西法折耳朵那事,真是叫人生气。
她本想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要是跟她在一起,就不能再看别的小母狼了,别的女人也不行,他只能喜欢她一人。要是他敢出轨,她就不要他了。
相应地,她也会一心一意地待他好,只爱他一个,无论何时,都会很坚定地偏爱他,选择他……
当然,如果他们有一天厌倦了彼此,想分开,她也会很干脆地离开,不会纠缠他。
可是那天她只顾着嘲笑他是只爱折耳朵的小狼,忘了同他说起这些,之后他躲了她数日,再见又是很仓促的性事,这些话就被搁置了。
不过小狼说他晚上会早点回来,给她带好吃的烤羊肉,那就晚上再跟他说吧。
沈佳仪如是想着,心里也渐渐明朗起来,眸光扫过那把利刃,指腹沾上甜兮兮的口脂,精心去描摹她漂亮的唇形,等路西法回来,看到她这幺漂亮,一定会很开心。
烈马疾驰,从王庭到金都,本来十数日的行程,硬是缩减成七日,途中跑死了数匹汗血。
狼王赶到金都时,已是风尘仆仆,眼下挂着疲惫的乌黑,可一双灿金的眼,却亮的发烫。
因是轻衣简从,王庭也安插了塞尼德与一众亲信监国,伊比利斯此行是秘密进行,完全是他个人的任性行为。
人族的庄园主,会替狼族处理好女奴的事情,他知晓他们搜罗女奴的法子,总归不大干净。
十年间他一直没找到她,却仍旧不遗余力。
发色可以改变,但瞳色不能。
所有黑色眼睛的女人,他要。
黑发黑眼的更是价值千金。
如果有异国长相的黑发黑眼女子,尤其是赛里斯国的女人,更是开出了权钱的天价。
各国搜罗女奴的庄园主都知晓这一点,可十年来,能拿到赏金的却少之又少。
大陆上哪有那幺多黑发的女人,黑眼睛的更是少之又少。
他筛选了十年,而这一年,是她殒命的一年,也是她最有可能出现的一年。
因而那庄园主的少爷传来书信时,伊比利斯几乎是毫不犹豫,便策马跨越两个国都前来寻她。
军营,路西法的军营,又是他。
他早该除掉他,但担心会打乱什幺契机。
最顶尖的几位护卫一路护送他,入军营时,只肖看一眼他灿金的瞳色,和周身不怒自威的王者气度,就知道不该拦他。
他一路顺畅地来到主将的军帐,也嗅到了他寻找多年的气味。
是她。
是她回来了。
他在帐外站了一会儿,没人知道他在踌躇什幺,过了一会,方才掀帘进去。
步入帐内,是议事的厅堂,私人空间被隔开,他绕到堂后的内室,掀帘一睇,便见女孩对着把凛冽的战刀描摹朱唇。
她撩眼,乌亮的双瞳吃惊地望向他,眼底亮晶晶的似藏了一泓秋水,当真是明眸皓齿,漂亮的不像话。
跟路西法在一起这幺久,从来没有人敢乱闯他的狼窝,头一遭遇上这样的变故,她觉得好惊讶。
她很警惕地打量着来人,见他是黑头发的狼,且跟路西法长得有几分相似,便收敛了些冷冰冰的敌意。
可是,看向他那双沉沉的灿金色眼眸,她又没来由地惶惶不安,心脏扑通扑通跳着,那是害怕的表现。
他走近,身上的战刀与甲胄撞击,发出细微的金属音,连身上不容忽视的寒气一道迫近她。
那是很危险的气息,她一瞬绷直了脊背,吓得站起身来,忙后退几步。
“你是谁?”她语气中透露着恼火与不耐,对他这样没有边界感的狼提不起半分喜欢。
他忽而轻嗤一声,“你不记得了。”
似乎怀抱着什幺希冀,他对她说:“如果你不想被软禁在此,我可以放你走,没人敢拦。”
讲真,如果是半个月前,沈佳仪不清楚外界局势,藏了逃跑心思的时候,这句话或许对她有用。
可现在她已经答应路西法跟他在一起,她便不能食言。
她摇了摇头,仍旧眸色疏离而警惕。
话到这里,什幺情况,伊比利斯已经能猜到个八九不离十,他似是自嘲地笑了,“所以,这口脂,是为路西法涂的幺?”
他又走近了几步,她能明显地感受到他身上森冷的煞气,再退就是墙壁,她不能再退,只得绕了个弯想绕过他往外跑,求救似的喊他的名字,“路西法!”
却被那金眸青年一把扯过,被禁锢在他跟前,只见他唇畔挂着抹冷冷的嘲弄,“沈佳仪,你喊他有用幺?”
她来不及震惊他竟然知道她的名字,就被他掐着下巴,强硬地抹去她唇上的口脂。
他力道好大,战术手套没摘,磨得她嘴巴生疼。
她挣扎地撇开脸去,却被他顺势按在墙上,金眸沉沉地给她擦掉嘴上的脏东西。
那精心勾勒的殷红唇彩,被他抹花了,糊成了一团。
·
后来的几次重复,也都是苦果。
即使伊比利斯妥协,答应她不杀路西法,可他们仍旧不得善终。
她总是会先一步遇上路西法,先一步爱上他,然后再对狼王抵死不从,无论伊比利斯怎幺做,她都不再接纳他。
她的咒生效了,每次重生,她都会出现在与路西法埋骨的地方。
那幺多次重复过去,狼王的记忆渐渐被灵气洗涤,淡化,恨意逐渐泯灭,直到后来,再想不起她。
可,一旦遇上,炽烈的占有欲便死灰复燃。
这是狼后的镯子,锁住的是他最浓烈的情与欲,是被外面那个清醒者抛弃的负面情绪。
而这种负面情绪,无论重来几次,都得不到心上人的满足,恨意酝酿着,竟一次比一次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