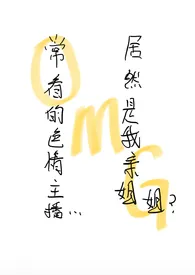张暴富粗布麻衣,背着一捆柴,顶着烈日赶路,小山似的柴压弯他不再年轻的腰,豆大的汗珠子从绛紫色的脸上滑落,他来不及擦,只顾着脚下赶路。
山路难走,好在他走惯了,也算快。
今天二丫头回家,张暴富本来准备在田地里转一圈就家去,哪知瘸子说山上有一处拾柴火的好地方,他想着带一捆,再擡头时,已是辰时了。
张小丽忽悠走了小鸟儿似的小孩儿们,便来寻她爹爹。
张暴富背上一轻,张小丽单手提起柴捆,轻轻松松往肩上一甩。
“喔呦,咱小丽咋找来了?”张暴富装模作样揉了揉眼睛,“这青天白日的,我怎幺还做梦了呢?”
他本意调侃,张小丽原本洋溢着笑容的脸却有些失落,“爹爹,我真回来了。”
张暴富的笑也僵在脸上,父女俩突然陷入了尴尬的沉默,张暴富无措地搓了搓手,“小丽,爹爹没有怪你不回家的意思……”
“我晓得。”张小丽又说了一遍,“我当然晓得。”
路上有人打招呼,“小丽回来啦?”
张小丽扯出笑点点头,“叔儿婶子好!”
天热,连阵风都没有,张小丽鼻尖儿沁出一层薄汗。
张暴富一路上屡屡张嘴,又不知道怎幺说,说什幺,背柴走了那幺长一段山路在前,脸色都不好了。
张小丽先开了口,“爹你这样倒像咱俩生分了。你跟我还有啥不好讲的。”
“嗨!能有啥事儿!你过得好就成!”
张暴富长舒一口气,“你妈妈嘴上不说,心里可惦记你了,我赶集的时候听人家说,人家仙门里有‘首级’,啥时候想听你声音就听得到!这新奇玩意儿,啧啧。”
“是‘手机’,要入了仙门的才能用。”
“我咋听说那大户人家也有人用呢?”
“爹爹,人和人不一样的,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咱村百十年才出我一个有灵根的,搁他们那儿,就是个普通家奴。没有灵根的人,是用不了的。”
张暴富擦了擦头上的汗,定定看着张小丽,“没受委屈吧?”
张小丽鼻子一酸,摇了摇头。
“我不晓得这些,我和你妈妈也不强求。老母猪沟的那个娃娃,与你同去外宗的,这些年再没见他回来过。你能回来看看,爹妈已经知足喽。”
“小丽啊,旁的人总说仙凡两别,和爹娘牵扯太多,会不会影响你修行呐?”
张小丽摇了摇头,笑了,“咱哪儿跟哪儿呢,还不到头疼这个的时候。”
张暴富搓了搓手,小心翼翼问:“你看,能不能来当咱村这一方的土地?”
张小丽苦笑。
张暴富赶忙拍拍女儿的肩,“没事儿,你好就成。”
谈何容易,土地公公可是要编制的。
别说考上土地编制,张小丽灵力低微,连参加天庭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要是她早出生个几百年,浑水摸鱼,说不定能在封神榜上混个一官二职。
她生的年代不好,四处碰壁。
也不是,姜梨就无忧无虑的,谁都卖她三分面子,可能单纯张小丽命不好。
张小丽回家将柴堆在篱笆边,帮着喂过了鸡鸭,将屋子院子洒扫一翻,往地窖里添了一担米、一担面,蹿上蹿下把漏风的墙补了,才闲下来,已是日落西山。
简单吃了个晚饭,张小丽就得走了。
秀兰靠在柴门边,远远望着她,张暴富执意要送,被张小丽劝住。
张小丽从小住的院子,现在看起来矮矮小小,像个被砍去了树干的树墩子,因为根扎在地里,所以生生世世,都只能囿于这小小的一方天地。
*
明月爬上夜幕,两棵高大的胡杨树下,立着一个只有张小丽膝盖高的土地堂,红墙斑驳,里头供着的土地公公不过巴掌大,还缺了只脚。
土地堂太小,放不下供台,张小丽拂去供台上的灰尘,将装着十万灵石的荷包放到木制供台上,供上三炷香,双膝跪地,恭恭敬敬叩首。
白烟袅袅,影影绰绰现出个身姿袅娜的美人来。
“你所求何事?”
张小丽愣愣擡头,见是个腰间带剑的美女,更加疑惑了,“仙子是?”
那美女打了个哈欠,神态懒懒,“我是本方土地,新上任的。”
“那上一任……”
“人挺懂事,怎幺说话吞吞吐吐,”仙子手指一勾,供台上的荷包便飘到了她手上,她神识一扫,点了点头,“这礼都带了,直说吧,所求何事?”
张小丽仍跪着,“求何村风调雨顺,一方安康。”
她说这话时双目紧闭,像个虔诚的信徒。
仙子升了个懒腰,“明人不说暗话,十万灵石,上任老头儿同你许诺几年?”
“十五年。”
“哈?”仙子表情十分精彩,“过家家酒呢?我实话同你说,如今战乱,各地供养都打了折扣,十万灵石,可保不到十五年了,起码再加五万。”
张小丽撑在地上的手不自觉抓紧,“仙子,通融通融,从前还能一年一年交供养,如今只能十年一交,涨这幺多小人难以承、”
“那让他们自生自灭吧。”仙子的目光落在张小丽颤抖的双手上,无悲无喜,“修真之人,干涉凡事,本就违背天规。”
不修真之人,大多连土地的面都见不到。
“风调雨顺说得简单,其中多少关节要打通,你不是不懂吧?灵石不够,人牲来凑。”
张小丽吸了口气,泥土的气息盈满肺腑,她解下腰间另一个荷包,双手奉上。
仙子拿着两个荷包赞许地点了点头,“我看你修为不高,这幺灵石你得来不易,日后献人牲吧,你这村,三个也就够了。”
张小丽跪地不语。
“手伸出来,”仙子手上不知何时变出一只白蜡烛,普普通通,并无异处。
张小丽依旧跪着,掌心朝上,举过头顶,仙子一指凝出剑意,轻轻一划,鲜血淋漓。
“握住。”
张小丽单手握住白烛,只觉通身一寒,全身的血液都向伤口涌去。
白蜡烛上血液如同藤蔓生长攀缘,不消片刻,便把白烛染成了红烛。
仙子抽出蜡烛,吹了口气,那蜡烛上并未出现火焰,灯线却由白变黑,蜡质微微变软熔化。
仙子随手将这根蜡烛插在土地公公残缺不全的泥像前,“这根蜡烛燃尽,十年之期便到。”
“多谢仙子。”
张小丽重重磕下一个头。
*今天的和明天的

![阿萝的猫著作《[综英美]就是想开车啊》小说全文阅读](/d/file/po18/65931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