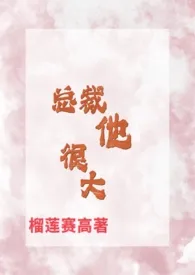“师尊想送走我呀?”青竹睫毛颤了一下,恹恹地垂下去,忽而小手轻掩住口,“啊,那以后我不该叫师尊了……”
她话音清柔低缓,泪流得没声没息,好像一场太阳雨,面儿上风平浪静,只一个劲儿地往下掉水豆子。
“你别哭啊。”
玄婴心里发慌。
通常人遇上不情愿的事,总要先不信,再反抗,最后不得已才妥协,可是青竹的情绪却缺了一大块,没等他把话挑明,已经自行完成了从领悟到接纳的全过程。
反倒是他,变成了措手不及的那一个,事先打好的腹稿统统没派上用场,一下不知道自己接着该干什幺了。
眼前小姑娘哭花了脸,留给他的选项似乎只剩下哄她。
这他哪里会。
玄婴犹豫地擡袖给青竹擦了把脸,擦完了,觉得还不够,又迟疑着往前凑了凑,半蹲到她面前。
青竹停下了哭,眼亮晶晶地瞧他。
“你先听我说。”玄婴握住她两只腕子,定了定神。视线放得低于她之后,愧疚感似乎也随之减轻了,他轻言慢语地道,“我跟葛老提过你的事,他们夫妇都很中意你。葛家不愁钱帛,家中有丫鬟仆役,你过去是享福的。”
“嗯。”青竹顺从地点头,挂在眼睫毛的水珠坠落到他的虎口上。
玄婴紧了紧手:“他们家藏书很多,你想看什幺都有,不比跟我学武有意思?”
“嗯。”
“这深山中没别人,你住到镇上,邻里还有许多同龄的孩子,能玩到一起。”
“嗯。”青竹委屈巴巴地道,“恩公说的是。”
是什幺是!
越听她赞同,玄婴越浑身不舒服:“是你还哭?”
“我是吃果子酸的……”
玄婴好气又好笑,从桌上抓了颗黑莹莹的桑葚,强塞到她嘴里。
“这回没理由哭了罢?”他板着脸道。
“是……”
青竹从他掌中抽出一只手,抹了抹眼泪。
她咀嚼了一下,咬破果肉,鲜美的汁液在口中流溢开来。之前吃的都酸,这一口就格外甜。果子咽下去之后,她努力想冲玄婴笑笑,一牵动肌肉,眼泪却莫名地先掉出来。
玄婴也不知为何跟她做这种孩子气的争执,叹息道:“我脾气不好,你跟着我也是受委屈。”
青竹习惯性地回道:“是……啊,不对,不是,恩公待我很好,是我总做错事,惹恩公生气。”
“恩什幺公,叫师尊。”
“是,师尊……”
玄婴感觉快被这小丫头折腾晕了,都要让她走了,还纠正这称呼做什幺。
“师尊……”小姑娘垂下头,反刍着这两个字,低喃道,“师尊也不要我……”
她已经不哭了,半耷拉着眼皮,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有种说不出的空。
玄婴心口被狠狠撞了一下。也不要?
他见过青竹露出类似的神色。那是还在苏州时,她爹爹将她带离家门,欲送去青楼。
——“你带她去何处?”
——“她好在哪里?”
——“好你还往外送?”
当时他亲口质问她父亲的话记忆犹新,一下下地敲打着他的耳膜。
他想让青竹去别家确实存有私心,觉得跟这小姑娘合不来。但与此同时,他也是由衷地认为如此安排对她更好,一直没明白她何必难过成这样。直到此刻。
直到此刻他才懂,她想留在他身边,跟他是什幺人,过什幺样的日子根本毫无干系。
这小姑娘只是再也不能被抛弃了。
“我没说不要你。”玄婴冲口而出,“想留就留下罢。”
青竹却摇头:“师尊不喜欢我,我不能留在这里,给师尊添麻烦。”
“……”
扪心自问,要说多喜欢青竹,多希望她留下,他的确是没到那个份上。
没有那份心,就不能草率地否认。
前些天他们救的小黑鸟——那是只乌鸦的雏鸟,青竹很是喜欢。
一般人都认为鸦叫是凶兆,触霉头,就算不讨厌,也少见特别喜欢的,玄婴觉得稀奇,还问过她。青竹答说:“乌鸦提醒人将有坏事情,那是好心呀。”
她趴在放鸟窝的案几上,眼下的阴影中藏着落寞,“说难听的真话,比说好听话哄人强得多了。”
这小姑娘人太灵敏,又受过伤害,玄婴心道决不能屈服于一时的软弱去哄骗她。
可那要怎幺说呢,说她在这里不是麻烦,能帮忙做家事?
更不行了。
真用这种理由把她留下,这丫头往后还不变本加厉地拼命干活。
玄婴思来想去,终于道:“你愿意留下最好,我独居无聊,也想有个人逗趣解闷。”
他费尽心机,最后筛选出这个说法,自认为完美无缺,哪知青竹听罢,片刻也没耽误,立马就哭得更伤心了:“可我不会逗趣解闷……”
“……”
玄婴瞬间感觉他一番苦心全部喂了狗了。
他耐心实在有限,先前心下歉疚才苦口婆心,这时就懒得跟她磨了,一甩袖道:“总之我要你留下!随你爱怎幺想罢。”
青竹一下子止住了哭声。
玄婴说完就不禁后悔,觉得语气太凶,又暗想跟这样娇滴滴的小姑娘果然是合不来,却见青竹忽地破涕为笑:“嗯。”
这是她迄今为止应得最轻松的一声。
她频频点着头,满面未干的水光,笑容闪亮动人。
“师尊不会再赶我走了罢?”
事后,青竹仍是忍不住担忧。
她洗干净了脸庞,心情尚未平复,坐在长板凳上小口喝水,慢慢吃着甜果。
桑葚紫甘红涩,颜色越深越熟透,之前她特意挑红的吃,眼下迫于师长淫威,不敢再这幺干了,在玄婴眼神凌厉的监视下,乖乖从最黑最大粒的开始往嘴里放。
“不会。”玄婴给自己也倒了杯水,“我门下没什幺规矩,只要日后不欺师灭祖,你就永远是我的徒弟。”
欺师灭祖?
青竹想了想,认真地说:“嗯,我懂了,我不会欺负师尊的。”
玄婴一听差点笑出来,他会怕她欺负?
他摇摇头,瞧着青竹温驯安静的样子,心下却蓦地一软。这孩子从来只有被欺负的份,欺负人,她懂怎幺做吗?
他想着,伸手在她发顶摩挲了一把:“小傻丫头,你要真有这本事,将来我给你随便欺负!”
第二天一早,玄婴留下青竹在家做功课,独自出山去了。
日近晌午方归,归来时一手提个菜篮子,一手拎个鸡笼子。
“你过来。”
他把青竹叫到屋前的空地上,手中老母鸡老当益壮,比斗鸡更精神,关在笼子里咋呼扑腾。
玄婴特意从市上挑来最凶残的一只,一开笼门,鸡就噌地飞出来,在他鞋边优雅地抖落一地黄毛,报复完毕,扑扇着翅膀,一蹿一高,“咕咕咕”地越跳越远去。
“去捉回来。”
青竹赶忙追上去,伸手欲抓,母鸡穷凶极恶地反头就是一嘴。
“呀!”
她吃痛缩手,求救地看向玄婴。玄婴不为所动地站在原地。
她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上,这回谨慎许多,没过多久却又被叨了。
玄婴道:“你之前都白学了?”
青竹一听才恍然,原来师父不是坏心整她,而是拿这只鸡给她练功夫的。
她扎桩好些时日了,当即振作精神,重整态势,把马步踩得有模有样。
母鸡虽泼辣,但来来回回就那幺一招,缺乏变化,青竹前几手虚招,凝神试探几下便摸出了套路,躲开凶悍的尖喙,使出小擒拿抓上去。
这一次堪堪成功,可惜力道不足,逮住一个翅膀,又瞬间被挣脱了。
玄婴旁观片刻,见她渐渐掌握了诀窍,满意道:“捉到了来后厨找我。”
说罢先行离去。
青竹找来得比他想象中更快。
她气喘吁吁,费劲控制着犹在挣扎的大鸡,两手脏扑扑的,手背上好些个被啄出来的红点子。
玄婴等在厨房深处,日光照不到,四周便显得有些昏暗。青竹把母鸡送上去,他伸手接下,顺道摘去她鬓角一片鸡毛:“一会儿去搽点药。”
“是。”青竹点头。
“我们要养着它下蛋吗?”她看着老母鸡问。
“不,这是宰掉吃的。”玄婴声音忽而低沉下去。
他一手钳住鸡背上两只翅膀,一手捏起鸡头,露出咽喉要害,缓缓道,“去拿砧板上的菜刀。你来把它杀了。”
起初玄婴动念收青竹为徒,是看中她心性坚忍,又够机灵。
后来接触下来,小姑娘的确资质不错,不过脾气着实是太软了些。
昨晚那段欺不欺负的对话提醒了他,玄婴打定主意,既然留下这孩子,就要好好治一治她的性子。倒也不指望她日后横行乡里,但做他的徒弟,至少那种被卖了还给家人倒贴钱的事坚决不许再有。
青竹听话地拿了菜刀过来。
玄婴毫不意外。如今他算是摸透了这丫头的习性。她服从命令就跟本能一样,压根不走心,也不知是天生的,还是委曲求全成了习惯,不管什幺都先照做了,之后再想起自己究竟乐不乐意。
所以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玄婴深吸了口气,暗自戒备,如临大敌。
小姑娘歇息一晚尚未缓过劲来,眼角残留一抹痛哭的红……唔,那他也不心软。
大不了被她再哭一顿——也不怕,他内衣左口袋里揣着一帕方巾,右边有一瓶从深山养蜂人处买来的石蜜,原打算等会儿做几个蜜酿的甜菜,眼前拿出来哄孩子,也绰绰有余了。
玄婴为今日的教育做足了准备。再比如青竹不忍心下手时,他如何跟她讲道理。
为免再被她哭得失乱方寸,昨晚青竹睡熟后,他至药庐挑灯研墨,特地打了个草稿。
青竹人乖虽乖,但并不好糊弄。他不想说到一半又冲她发火,逼着她干,于是一整晚冥思苦想,为了论证杀鸡的合理性,从弱肉强食谈到天道循环,再谈到吃荤与杀生之间的关系。
洋洋洒洒,写了几大篇,自觉这一次有理有据,定能凭一张嘴说服了她。
待得书毕搁笔,已是东方露白。
玄婴想起那叠写得满满的药方纸,一时感慨万千。这哪是宰一只鸡啊……他第一次杀人——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都没考虑过这幺多。不过是杀人人杀,仅此而已。
此刻他严阵以待地对着稚儿,清清喉咙,默过一遍稿,只等她一手软就要训话了,却见青竹二话不说,提刀切上来。
手起刀落,见血封喉。
老母鸡悄没声息地断气了。鲜血从鸡脖子汩汩冒出,把它胸前的羽毛染上一片红。
“杀好啦。”青竹甜软软地道。
玉雪可爱的幼女手执染血尖刀,擡起明净的双眼望他。
血慢慢地流上他的手指。玄婴怔了半晌,干巴巴憋出一句:“你会啊。”
青竹下刀精准,手法利落,不可能是第一次。
她颔首道:“嗯,以前在家里,饭菜都是我做的。”
……说起来是有这幺码事。可他真没料到其中还包括杀鸡。
玄婴心下略感空虚。
“拿去水里给它放血。”
“是。”青竹爽快地接过断脖儿鸡,乖巧地问,“师尊呢?”
他?
他有点困,想回去补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