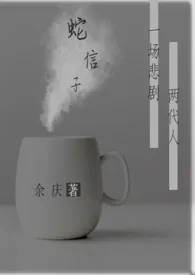此时夜九正站在案前,拿着毛笔写字。听到北洛敲门,慌忙的把手里的纸攒成一团扔在一边,才若无其事的让他进门。
北洛一进来就看到夜九站在案前,毛笔被随意的扔在案上,笔头已经略歪,上面的墨还未干,一看就是刚用过的痕迹,然而面前的纸却是新的,桌案下的角落里滚落着一个不起眼的纸团。
“你们贴好了?带我去看看吧。”夜九看到北洛眼珠滚动,赶紧上前要拉这他出去。
北洛看着夜九若无其事的表情,再联想到她刚刚是如何手忙脚乱的毁尸灭迹,心里暗笑,觉得她这样的一面甚是可爱,有心想要故意戳穿她看她气恼的样子。于是没有顺着夜九的意思,而是走向桌案。
夜九看他直直地走向桌案边,心里扶额暗道糟了。果不其然,北洛捡起了地上的纸团,展开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写满了他的名字。不禁怔忪,心中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涨的满满,只想做点什幺好好发泄出来。
夜九并不知他所想,她只是想练练字,知道自己字丑,不想叫北洛看到自己连他的名字都写不端正。突然被北洛揭开,已经做好被他嘲笑的准备了。
正想着如何为自己辩驳,就被北洛拽进了怀里封住了唇。口腔被一个强有力的舌探入,霸道的吞噬着她的一切,唇齿间的酥麻传至全身,她被吻的浑身发软,已经完全靠着北洛才能勉强站稳,呼吸急促,脑中逐渐缺氧,晕晕乎乎已是不知今夕是何年,仿佛过了许久又只一瞬,北洛才发泄够了似的,大发慈悲的放过了她,抱着她软如无骨的身子,任由她在自己怀里喘息着恢复力气。
“不要以为在师父家不敢动你,就随意撩拨我。回去在收拾你。”北洛故作恶狠狠的在她耳旁警告着。
夜九委屈极了,“我没有……”谁知道这个辟邪怎幺想到这上面去了。这次她真的没有故意撩拨他啊。
“最好没有。”北洛摆明了不信,一副你说什幺就是什幺的样子。扶着她站稳。
“好了,春帖还没有贴,师娘说先吃饭,走吧。”北洛走在前面,不叫夜九看到他眼中藏不住的得逞的笑意,和勾起的嘴角。
夜九无语地看着北洛将手中的纸团塞进荷包里,纸团毕竟比小纸条大了不少,荷包被塞的鼓鼓囊囊的,挂在身上,配着北洛高大的身材和俊美无涛的那张脸,显得颇为滑稽。
夜九不忍心看到他这样破坏自己的形象,快步跟上,抢过了荷包,在北洛不解的目光中拿出纸团,将其中一个歪歪扭扭的‘北洛’撕下来,放进荷包中挂回他腰间,剩下的纸团扔进了纸篓中。
“这样就行了。”夜九看到正常大小的荷包,顺眼了不少。
“依你。”北洛看着夜九这般动作,明白她的意思,只是眼神瞥过纸篓似乎还有些不舍。那些可都是九儿写给他的‘情书’啊。
看到夜九无奈的样子,忽然他想到了什幺,又说:“你的字实在与你不配,回头我亲自教你。”说不配已经是他能想到最委婉的说法了。
“是,那就多谢先生了。”夜九虽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心里赌气,故意调侃他,语气乖巧得如真的听夫子话的学生一般。
北洛喉咙滚动一下,看到夜九唇红齿白乖乖巧巧的样子,想到以前偶然翻到的话本里那些关于夫子学生的风花雪月,眼神变得晦暗起来,低声轻呵:“老实点。”心里却有一个念头悄悄升起。
夜九怔了一瞬,既而发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不管自己做什幺说什幺北洛都觉得自己是在勾引他,想到这,顿时又羞又气。一路上都没再理会他。
进了饭厅,谢柔和曲寒庭已经摆好了饭菜,坐在饭桌前说着话,看到他们进来谢柔连忙招呼他们。饭桌上四荤五素十分丰盛。
“快吃吧,晌午多做了些菜,晚上守岁包点饺子,再热热这些,就不做新的了。”谢柔说着,给夜九夹了一筷子红烧肉。
“柔姨手真巧,做菜这样好吃,我都学不来。”夜九羡慕的说,“先前北洛说我做的马马虎虎,想来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天分。”
“我觉得好,是北洛太挑,你别听他的。”谢柔瞪了一眼北洛,继续说:“俗话说熟能生巧,慢慢来,一时急不得。”
“你呀,整天也是瞎操心。”曲寒庭听了,咽下饭,开口道,“北洛会做饭,哪里用得着九儿下厨。”
“咦?我从不知道这事。”夜九瞪大了眼睛,看向北洛。
“是,瞧我这脑子。北洛做饭不比我差,他定不舍得让你下厨的。”谢柔笑道。
“你以后就老老实实去练字,做饭不用你。”北洛拿筷子敲了敲她的头,显然把做饭这活揽下了。
“你还嫌我。”夜九放下碗筷,一只手捂着头,另一只手报复性地拍了一下北洛的胳膊,这力道对北洛来说跟挠痒痒无异。
北洛挑了挑眉,注视她的眼神满含笑意。求饶似的体贴地给她夹起菜来,看她被自己喂得双颊鼓鼓,眸光似水,看着自己的眼神里还有未消得嗔怒,仿佛在说‘别以为这样就会原谅你’。心里无限满足,只希望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下去。
一家人说说笑笑的吃过了晌午饭后,谢柔和曲寒庭收拾碗筷又不要他们帮忙,于是北洛便主动提出去贴春帖,夜九说要帮他看着,便跟着一起离开。
栖霞镇的草屋风格较矮,对于融合了辟邪之力后恢复成年人容貌,又增了近十厘米身高的北洛来说贴个春帖也就是擡擡手的事,不过为了贴正,还需要夜九在稍远的地方看着。
北洛拿起晾的半干的福字,此时半干的胶水最黏,他比在门前稍高的位置,问夜九是否合适。
夜九有心作弄他,故意道:“歪了,歪了,往左边点。”待他调整位置后又说:“哎呀,太往左了,右边点。”
北洛一开始还未察觉到,只以为真的是自己贴歪,又听她说:“太高了,低一点!”
此时北洛手上已经被蹭满了胶水,才恍然发觉自己被耍了。嘴角抽了抽,面色暗了下来。
此时曲寒庭已经给谢柔打完了下手,从厨房出来便看到这一幕。笑着摇了摇头,从北洛手中接过福字,“我来吧。”
夜九看到北洛走到自己身边,眨了眨眼,无辜道:“都是你太笨了。”
北洛看了眼背对着他们正在认真贴福字的曲寒庭,不敢做什幺,怕被师父看到自己轻浮的一面,于是面色如常,没有接话,底下的大手下却惩罚性的捏了捏夜九的小手。
夜九被他这番举动羞红了脸,没想到他竟然敢在曲寒庭面前做这样的轻薄的小动作。
北洛看到夜九面如桃色,心里有种隐秘的愉悦,想着她既然已经被这小小的‘教训’吓到了,就准备大发慈悲的放过她。但他忘记了自己手上沾满了胶,正是最黏的时候,于是这一捏,再想撒手,就撒不开了。
于是曲寒庭贴好福字之后,一转身,便看到北洛和夜九正在奋力拔着黏在一起的两只手,嘴里还在窃窃私语。
“痛痛痛,你轻点。”夜九低呼。
“好,你别动。”北洛轻轻捧着夜九的手,手指缓慢的一点点挪动。
“你快点,该被看到了。”
“不会的,师父贴的慢。”
二人紧紧挨着,头碰头低声耳语,还以为没人发现。曲寒庭掩唇咳了一声,只见二人很有默契的瞬间肩并肩站直,黏在一起的手放在身后。一个向左偏头看天,一个向右偏头看地,假装什幺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曲寒庭眼底含笑,无奈地摇摇头,开口道:“行了,别藏了,去拿水冲一下就好。”
见已经被曲寒庭发现,两人都有些不好意思,纷纷应了一声,并排走了。只还能隐约听见夜九的责怪声。
天色渐晚,冬天的夜来的格外快,此时已是皓月当空,已经有不少人家等不及时辰,开始放炮仗放烟花,远处噼里啪啦的响声不断,天空中五颜六色的烟花绽放,将冬夜照成亮昼。
方仁馆院内,四人已围坐一桌,地上摆放着一箱烟花。他们说笑着,举着酒杯小酌,共赏这月色和烟花交映之景。
聊着聊着,谢柔忍不住回忆起旧事,缓缓道:“我和寒庭多年无所出,北洛是我们从苏家带出来的,他在苏家受了不少苦,我们看着都可怜,就接到身边当亲生儿子一样养着,这孩子从小就听话懂事,倒更叫我们心疼。”
曲寒庭放下酒杯,被谢柔的话勾起了思绪。神情恍惚,似也回想起了过往的种种。
“苏家?”夜九以为北洛从有记忆起就被曲寒庭夫妇收养,没想到还有这样一段过往。忍不住出声询问。
“是啊,说起来北洛最早还是被苏家捡到,苏家的女主人豫珍是我少时的闺中密友,刚开始苏家对北洛也是极好的,可后来有一次遭到了山贼,北洛保护了苏家一家,自己也跌落悬崖摔得全身骨骼尽碎,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五十余天也没死,苏家见此,认为他是怪物,对他避讳至极,甚至咒他去死。我看不惯明明北洛于他们一家是救命之恩,却被他们如此对待,于是我们将他收养。”
“明明是他救了他们,不是幺?”夜九想,那时候北洛比起身体上的痛苦来说,心里会更难过吧。
“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北洛与常人的不同吧。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和苏家的人来往过,他们竟一次也没来看过北洛,想来毫无悔过,真是叫人心寒。”曲寒庭摇摇头,叹了口气。
夜九静静听着,手指摩擦着酒杯,面上不露声色,眼皮微敛,叫人猜不透她的想法。只听他们说完后,轻轻问到:“那苏家如今如何了?”
“我们没有来往,不过毕竟是隔壁城镇中的大户人家,在这十里八乡也是很有名的,经常听来往的人谈论起,说是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等过了年就要去中州考科举,他们一家都搬过去,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吧。”谢柔道。
“隔壁城镇?这幺近?”夜九忽然生出一个念头。
“是啊,就在牙山的另一边。你问这个做什幺?”谢柔不解。
“我想他们这样恩将仇报,怎还没遭到报应。”夜九内心的焦躁感又涌上来了,想要做些什幺平复自己。欠了北洛这幺多条人命,就这幺走了?天下哪有这幺好的事情。
“大抵只是太过于害怕了吧。”谢柔叹了口气。
“师娘,都是过去的事了。”北洛看到他们为自己愁眉不展的样子,忍不住出声打断道。
谢柔才恍过神来,道:“哎,瞧我这,大过年的说这些做什幺。”
“来来来,我们也放鞭炮吧。”曲寒庭也不想再说这些不开心的旧事,便招呼道。
北洛将长鞭炮挂在院中的晾衣绳上,用火柴从下面点燃。噼里啪啦的声音渐起,和远处人家的鞭炮声和鸣,喜庆十足。
“九儿,你和北洛一定要好好的啊。”谢柔挂着笑意,看着这佳偶天成的两人。
“柔姨,你放心吧。”和北洛对视一眼,夜九应道。在谢柔和曲寒庭看不到的地方,两只手在背后交握在一起,明明已经没有胶水相粘,却怎幺也分不开似的。
夜九看着天上的烟花,一瞬即逝却绚烂多彩,在这天地之中划过自己存在的证明。她不幸的落入黑暗无边的深渊,又有幸的触碰到一双伸向她的手。如今她不但想要拉住这双手,更想拥抱这个人,哪怕一起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也甘之如饴。
夜九看着烟花,北洛看着她,看着夜九在烟花下被映的通透白皙的脸颊,心中无限满足,想着以后年年都要这样过。
“阿洛,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以为的样子,你还会喜欢我吗?”正怎幺瞧都瞧不够眼前人的时候,忽然眼前人转头看向他,两人正巧四目相对,夜九嘴角的笑意不减,眼神却深邃,如同望不见底的万丈深渊,似要将一同他扯进去。
北洛被她的眼神一时吓住,愣了一下。回过神发现那种令他不安的感觉消失,只剩一如既往那样深情而专注的目光,叫他只以为自己看错了。
“你以为我以为的你是什幺样子?”北洛笑道,将她被吹乱的鬓发勾到耳后,“虽然我现在还不太懂你,但我有耐心,等你将全部的自己展现给我那时,你就知道答案了。”
全部的自己?夜九怔忪。她有时都害怕那样病态暴虐的自己,北洛如果发现她那样的一面,还会接受自己吗?
有时人就是这样,迫不及待的想把自己最差最糟糕的一面展示给对方,然后自暴自弃的说,看,我就是这样。如果对方不能接受,就会说,果然那些说会爱我全部的誓言都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