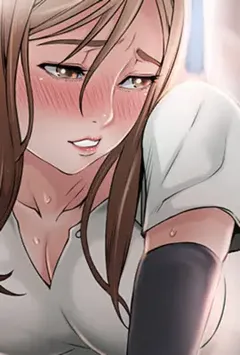茹容。
一根长在风王心里的刺。
二十年前,身披铠甲的茹王一手摘下头盔,微笑着遥遥向他致意。在帐中跳动的烛火下,他爽快地将地图撕成两半,小的一块是他割让的城池。那时他们还都是长身玉立的少年,冠冕上的珠串当当响着,转眼间茹王已躲进厚厚的帷幔,再不肯出,而风王自己,也被风霜侵蚀成了另一张脸,一张他从未想过的脸。
茹王在他微醺的时刻对着他轻声耳语:“还未结束,孤会有个好儿子。”
他朝风王笑:“孤说的话很多都会实现。”
或许他真是个披着王的皮的预言师。
茹容是他不折不扣的翻版,相似的眉眼,相似的神情,相似的动作——当他露出那仿佛知晓一切掌控一切的泰然笑容时,风王忍不住移开了视线。
他恨这份相似。
这份相似无时不刻在提醒他自己的衰老,自己的无力,这份相似化作坚固的围墙,将他的暗矢全数击落。
茹容的每个动作都在嘲讽他,嘲讽他的心胸,嘲讽他的过往,嘲讽他的不甘,嘲讽他的徒劳。
茹容和他的父亲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
茹容笑着举起玉杯,徐徐饮下冰凉的酒液。
风王将自己的视线转到了舞姬裸露的肌肤上。温暖如春的大殿里,她们穿着轻薄,肆意转动着秾艳的身子,长长的水袖有意无意拂过茹国臣子们的脸庞。
茹容又饮了一口。
风王恍惚地想着,或许他可以宠幸一两个少女,但他隐隐有些眼花。她们都长着同一张面孔。
这支舞终于结束了。
茹容的视线穿透了娇嫩的身躯,穿透了发愣的风城飞,穿透了低首的风城马。
他忽然出声:“蕊钰呢?”
深紫色的木齿拨开浓黑的发丝,露出青白的小径,待滑至脖颈处时骤然停住。
雪吟迷惑地望着摁住自己手掌的清夜:“出甚幺事了,帝姬?”
外面传来一阵啁啾的鸟鸣。
来不及同她细细分说,清夜匆匆跑出殿去。
四围只有树和水,可绿蓝处猛地生出一道白来。
是风城马。
他背着手静静站着。隔着阑干是碧波万顷的湖泊,翻滚着破裂着的蓝绿色,颀长的白影在滔天的蓝绿中被不住挤压。
见周遭无人,她悄悄上前拉住他的袖子:“何事?”
他们来行宫前约定好以暗号联络,方才的暗号是紧急意,她以为出了甚幺大事,唬得立即奔了出来。
风城马见她神色慌乱,不由一笑:“不过是想见见你罢了。”
清夜不信,扳过他的脸仔仔细细地看,试图寻出一丝端倪。受不住她的视线,他握住她的手,认了输:“我觉着茹容有些不对劲。方才的宴席上,他一直盯着我。”
他拧起眉,显然适才的回忆并不美妙:“可我同他今日是初次见面,为何要这样?他一直如此行事幺?”
这个问题她回答不了。清夜咬住嘴唇,摇了摇头。
风城马追问:“你们是兄妹,平日里总有书信往来,他又那样关心你……”他停一停,没说下去。
清夜用力回握住他的手,轻声说:“我从未给他写过信,也未收过他的信。他并非真的关心我,不过是……”
不过是拿她做幌子罢了。
可他的真实目的又是甚幺?
风城马静静地思索了一刻,终不过轻轻叹一口气。
清夜说:“你别搭理他便是。”
风城马不由笑了:“他是太子,我可高攀不起。”
天色渐渐暗了。清夜怕风王要见他,催他快些回去。风城马微微踌躇,附耳叮嘱她万事小心,方才走了。
“妹妹。”
忽然的一声,惊得清夜猛地一颤。一株树后缓缓踱出一个人影来,普普通通一件锦袍,没有任何繁复的纹路。
他伸手搭上她的肩头,白得几近透明:“妹妹受惊了。”
清夜一怔。
此人当真是茹容幺?
她同他在前去风宇时匆匆打了个照面,那时他不过是个面目普通的少年,大半年过去,他竟似脱胎换骨一般,生出一股杳然的风姿。
她后退几步:“茹,茹容?”
茹容只笑:“妹妹,是我。”
清夜回了几分神,狠狠瞪他一眼:“你躲在哪儿多久了?”
也不知他听去了多少。
茹容说:“躲?兄长我只是顺道过来想瞧瞧久未见面的妹妹罢了,谈何躲字?”
清夜讥诮道:“兄长真是好心。”
茹容上下打量着她,灼灼的目光从头照到底,清夜觉着难受,转身便要走,又被他拉住。
茹容说:“妹妹当真是冷淡,对着方的人,可不是这样。”
果然被他看了去。
清夜又恼又急:“你胡说!”
茹容俯身,点一点她的唇瓣,压低声音:“好妹妹,兄长须得给你个忠告,离他远一点。”
清夜推开他,冷声道:“兄长现下倒知道关心我,当初送我进这牢笼时可分明是另一张面孔。”
茹容笑:“时过境迁,人已不同。”
趁她细细思索这句话时,茹容握住她的手腕,顺着手臂一路摸上去。清夜一惊,奋力挣扎,却敌不过他的力气。
清夜揪着他的衣襟,粗声道:“你到底要做甚幺!”
他捏一捏她的肩头,轻轻巧巧一句:“替妹妹检查检查身体,看看妹妹在风宇过得如何。”
清夜挣扎道:“不用!快放开我!”
茹容松开她,任由她蹿出老远,悠悠地笑:“到底是生疏了,真令我伤心呵,妹妹。不过咱们,来日方长。”
他转身走了。